在我村子与隔壁村子的交界处,有座叫白马营的不高山头,那里树木茂盛,葱葱郁郁,遍布着不少知名药草,至于飞禽走兽,更是数不胜数。纵然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却鲜有村民敢进去。即便是靠山吃山的药农猎户,也不例外,路经此地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绕开。
追其原因,这是由于白马营那些灵异事件闹得太凶造成,比如无头女鬼、青面老人、红头怪等等,被村民们传得有鼻子有眼。至于是真假,我只信两成,毕竟国人以讹传讹的本事,可是有着千百年优良传统。特别在缺乏娱乐项目的农村,三大姑八大婆们,更是以造谣为乐。
我曾堪舆过白马营的地貌走势,那里形如漏斗,上宽下窄,这本倒是块极难得的聚财宝地,进可收财退可守财,但由于四周山体,都比它高出二到三十米的缘故,挡住了风水口子,又遮住了大部分阳光,导致财气进不来,阴气散不出去,活生生把风水宝地,变成了聚阴之所。
聚阴地,顾名思义,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当然,这里的污垢是指妖魔鬼怪。一旦先人葬在聚阴地,后人三五年内必定遭殃,轻则破财,重则损丁。我曾迁过不少这样的阴宅,有些死者甚至还发生逆生长现象,不但尸体没有完全腐败,而且指甲头发还明显增长不少。在阴阳界聚阴地,也叫做养尸地,因其特定环境形成的风水局,这些鬼魂会被困于其中,备受煎熬。只要风水局没发生改变,这些鬼魂都难以前去投胎,除非有道之士行法强催。
死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活人。我们当地有去过白马营的人,大小运正在起势、还有身后有神灵护佑的除外,那些八字弱、逢流年的人,回家之后不是感冒发烧一场,就是一连几月下来的不顺。其中,最倒霉那人还要属我们邻村那名陈姓男子,他从白马营回来后不到三个月,便出车祸走了。
这陈姓男子名叫真塘(化名),是我妈本家人,按辈分我还得喊他表哥,不过已经出了三服。陈真塘没有正当职业,靠山吃山。据他妻子李氏事后回忆,他那天去白马营挖牛奶根的时候,恍惚之间,曾听见背后有人在喊他小名。知道他这个小名的外人没几个,他当时还以为是碰见熟人了,下意识还回应过一声。只不过当他转过头来,身后却是空空如也,阴森森的山林中,只有风声依旧。陈真塘在他们村里可是出名的大胆子,不然也不敢一个人上山讨活。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心理,他挥舞着锄头,继续忙活手头活计。
“阿呆,阿呆。”
半小时过后,就在陈真塘满载而归之际,突然再次听到背后有人在喊他的小名。这次声音离他很近,仿佛就在耳边响起。与此同时,他还听到边上传来人为走动的声响,不时有细小的树枝咔嚓咔嚓被人踩断。他连忙转过身来,想一探究竟,但与先前一样,幽暗的山头上,莫说是人了,就连道鬼影子也没有。这前后两次喊话,前面那次他并没有留意,后面这次则是道凄厉的女声。
有些心生惧意的陈真塘,一手提着锄头,壮起胆子吼道:“奶奶熊的,你们这些小鬼,信不信老子一锄头砸死你们。”
他这招骂鬼之法,是否有效,答案肯定是有。人怕鬼三分,鬼敬人七分。但如果你运道正处于落势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别说是骂了,即便是你手持柳鞭,头戴道冠,那些牛鬼蛇神也不会惧你半分,有时更会适得其反。
正这时,刚骂得兴起的陈真塘,忽然望见几米开外的那棵百年大榕树下,不知何时,站着一位身着素色古装的无头女人。那无头女就这样诡异的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就在他想要定睛再看时,对方却在他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他是头一回遇见如此骇人的事情,之前在山上虽说也碰着过一两回灵异事件,但与之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
回到家后,他一连几日都往寺庙里跑,典型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过这佛脚并不是他想抱就能抱,一切皆有命理注定。神佛冥冥中的威灵,在其中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你三更必死,他们帮你留到五更,这已经算是能力上的极限了。不然的话,所有病入膏肓的人,都跑去寺庙烧香拜佛求庇护,那地府之下,又有谁替阎王爷表演上刀山抽肚肠的把戏呢?
那阵子,陈真塘常常梦见白马营上一晃而过的那名无头古装女,或站在桥头、或站在他家院门口,静静地朝他招手。每次他被这骇人梦境惊醒后,总能感觉到房间内有外人存在。当他打开电灯后,这种强烈的感官又会随之消失。除此之外,他还隔三差五的闻到一种香味。这香味很淡很淡,有时出现在院子内,有时出现田埂边,几乎无处不在,但若是他去细闻的话,又会诡异般消失。陈真塘对这香味并不陌生,十几年前他在他奶奶老旧的化妆盒里就曾闻到过,这是古人常用的胭脂香。
陈真塘妻子是位无神论者,最初并不相信他的鬼话,还以为是他那阵子劳累过度产生出的幻觉。有几次半夜被他吵醒后,还骂他发什么神经。直到某天晚上,她起夜时无意中透过卧室的窗户,望见外头两米高的院墙上,正坐着一位穿着素色古装的无头女。那无头女的两只长脚,还诡异的吊在半空中来回晃悠,像是没有一丁点力量般。惊吓之余,她连卫生间都顾不上去上,赶忙回屋摇醒陈真塘。待他们夫妻打着手电筒走出屋门时,那无头女早已鬼去墙空了。
里里外外寻找一圈,陈真塘夫妻在无头女先前坐过的那堵院墙下,赫然发现几串小巧的脚印。这些脚印很轻,前浅后深,像极了古人所穿的三寸金莲。如果不注意去看,根本难以发现。
第二天一大早,被吓破胆子的他们夫妻,提着水果酒品等礼物,跑去拜访他村里的某位神婆。其实,从白马营回来后,陈真塘就曾拜访过她。只不过由于他妻子几年前曾辱骂过对方装神弄鬼,到处敛财,所以那神婆也就没给他看事,而是放下话要他妻子到她家神坛前上三柱香,她才能够既往不咎。
被那神婆婉拒后,陈真塘并没有去找十里八乡的其他神棍问事,而是按照邻居老头教他的土法,在家门口烧纸钱讲好话,以求那无头女鬼高抬贵手。这种土法在民间很常见,对于那些只是讨纸钱花的孤魂游鬼很有效果,只是放在无头鬼等此类大凶物上,明显没有多大作用。虽说如此,但自从烧完纸钱后,陈真塘倒是有一阵子没再梦见那无头女了。如果不是昨晚她在院墙上现形的话,他还以为误打误撞之下,真把对方送走了。
陈真塘村里的那名神婆,属于出道修功德类型(北方叫出马仙)。大字不识一个的她,只会请僮看事,并不会行坛起法这些。她所有断阴阳的本事,都得靠她家供奉的神灵,即便是最入门的采吉问纳也一样。她家供奉的主神是位黑面将军,看事非常灵验,名动十里八乡,到她家求解阴阳事的人络绎不绝,我看得都眼红。
那神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帮一对夫妻找回他们的被拐卖三年的儿子。当时上她身的黑面将军,并没有要求那对夫妻去具体位置找寻,只是简简单单说了一句:“二到四月这两个月份间,你们农历十五前搭嘟嘟去蜀地(坐车,福建一带神灵,讲车子一般都是说嘟嘟),就能找到孩子,错过了这辈子就不能再遇着了。”果不其然,他们夫妻二人,在第四次前往重庆的途中,找到了他们的小孩,还顺带抓到了拐卖他们儿子的四川籍男子。
到了神婆位于村口的家中,陈真塘妻子不知是诚心,还是敷衍的向那神婆道完歉后,那神婆虔诚的朝神坛一拜,坐在太师椅上,声音清灵的唱起了请神歌谣:“三柱清香向天地,红花堂前拜老君。一请闽东吴越王,二请灵山黑元帅……速来坛前显威灵。”
每个神灵,都有专属的请神歌谣,这些歌谣大多是根据他们生前在民间的事迹编撰,比如闾山教陈大奶,她的请神歌谣,必定带有斩白蛇求雨这段。比如师法主杨师公,由于他身前有疾,请他的时候,如果没唱腾云坐桥一路来,神兵天将尽相送,兴许他就不会上身。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只要与供奉的神灵契合度高,请他们上身的话,或许只需要一个哈欠就够了。文中不过是为了添加真实性,才多写一笔。现实中我见那神婆请黑面将军,根本就没多费口舌,一拍膝盖,就自行上身了。
用古调唱完那段请神歌谣后,那神婆眼睛忽然一睁,随着身体剧烈摇晃,整个人的气质,顿时为之一变。举手投足间,尽显威风堂堂,杀气凛凛。她接下陈真塘递来的茶水,大手一挥,问道:“民间凡子,何事请某?”
站在神坛下方的陈真塘,连忙将近来发生的灵异事件,一五一十的复述了一遍。那黑面将军听完后,恶声恶气骂道:“这妖孽道行不浅,自某保这地境几百年来,她至少害了不下八人,看某不把她打得魂飞魄散。”
正神行事比较顺应天道,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斩杀牛鬼蛇神,一切皆有因果轮回。无论是神是鬼,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若是世间无灾无难,那要满天神佛又有何用?很显然,眼下黑面将军放出的豪言,纯属是为了找回场子罢了。有时候神灵比凡人还好面子,特别是将军元帅之类的武神。
闻言,陈真塘神态顿时为之一松,低着头道:“那还请将军多多劳心,我被她缠得都有睡眠恐惧症了。”
黑面将军点点头,道:“生辰八字,某帮你推下运程。”
待陈真塘点头哈腰的将生辰八字报上后,黑面将军掐起手指,盯着空无一物的手掌出神半响,才道:“流年犯阎口,难怪会见鬼招魂。”
阎口通俗点的说法,就是死劫。每个人的一生,至少要经历一个阎口,有些人刚出生就会逢着,所以早早夭折了。有些人则是临老时才会见到,死成了喜丧。这里边的不公平处,只能用一个命字来囊括。生不怨天,死不怪地,万般皆由命的命。
至于黑面将军后边提及的鬼招魂,那是代表着血光之兆的几个大凶梦之一。能做此梦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大运低到极致之人。这种梦境没有特定的场景或人物限制,最大的特征就是梦见亡人站在一些意味分离的地方朝你招手,比如桥头、车站、长亭等等。当然,这得配合生辰八字去推算,其中不乏只是巧合梦见,或是太过思念过世的先人。我就曾碰着过几回,印象最深的是位大光头,他那几年运道盛到即使我使邪法催鬼神害他,都没有多大效果。
阎口又见鬼招魂,这基本属于无解。作为外行人的陈真塘,自然不懂其中的门道,忙问道:“那该怎么办?”
黑面将军生前就是因愚忠而死,被黎黎百姓供奉成地境神后,依旧保持着那耿直的脾性。他没有遮遮掩掩,直接开门见山道:“如果只是寻常的鬼怪作乱,某倒有术可解,但你身上这个阎口,已经到了必死的地步。”
自古忠言逆耳,陈真塘妻子见黑面将军这般说法,误以为是那神婆还念着旧怨,故意刁难他们。于是牛脾气也犯了,甩下几十块看事费用,便气鼓鼓的拉着陈真塘回家去了。
这事过后还没有一个礼拜,某天,陈真塘妻子的娘家人,突然给她打电话,说是她父亲在田里晕倒,要她马上回家一趟。耐不住妻子催促,陈真塘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一路上风驰电掣的奔跑在县道上。在经过一个路口时,边上突然窜出一只野猫。他刹车不及,连忙将车头往右一甩,顿时失去重心,侧滑在地,砰的一声撞到边上的护栏。
也该陈真塘命中应有此劫,戴着安全头盔的他,头部竟不偏不倚的卡在护栏中间部位。被卷起的不锈钢边缘,割破喉咙,还没坚持到120到达现场,就当场流血而亡了。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他妻子,被甩出护栏外面石堆后,反倒就擦破层表皮,额头有块淤青,并无其他大碍。正所谓命大死不掉,命小无处躲,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谁也无法摆脱。
由于我家附近村庄,就我跟另一位法师会做红白法事(供奉黑面将军那个神婆不会),而我口碑一直又不错,所以陈真塘的后事,理所当然的就由我来一手操办。陈家说富不富,说穷不穷,在村里有一栋两层楼的小楼房。到达他家后,我简单用过些酒菜,就比手划脚的使唤他家人,把院子内事先备好的七张八仙桌摆放整齐,叠罗汉似上中下叠成三层,下面放三张,中间放两张,最上面则放一张。余下的那张桌子,则摆在正下方,用于陈放铃铛、号角、令旗等法器。
这种摆法是用于起法坛,法坛越高,术法也就越灵验。有些法事比如解鲁班煞、斗法等等,甚至还要将法坛设在最顶楼的天台位置。但红白这类简单法事,就不用如此大动干戈了。若不是陈真塘死于非命,我只需在大厅正中间位置,摆一张八仙桌便已足够了。
见陈家人三下五除二将八仙桌摆好,我便叫来边上一名小伙子让他去打一盆清水。趁着这段间隙,我心随笔动,意守灵台,一连画了三张净身符。将黄符烧置成灰放于盆中后,我大声叮嘱在场所有人,今晚凡是需要给我法事打下手的人,都必须在盆中净一下双手。与此同时,我还让属猪属羊的人避让,因为他们生肖与死者对冲,若是在场的话,不但会影响到法事的成效,而且还有可能惊扰到陈真塘的亡灵。
做完这一道预备工作,我从随身携带的黄色大挎包中,恭恭敬敬请出师法主杨师公的小神像,放在八仙桌最高那层的中央位置,并摆上一个香炉,插上三柱明香。杨师公是我施法时的坛中主神,明里由我来行令,暗里由他去布法。他小神像前的那个香炉,法事结束前无论如何都不能断掉香火,否则整场法事就有可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等陈家人将鸡、猪肉、米饭等贡品,依次摆上各个叠起的八仙桌,这场法事也就开始了。我虔诚的捧着一把清香,朝天地四方躬身一拜后,沿着陈家院子外的那条村道,隔半米插三柱,一直插到我法坛前。这做法是为了恭迎天兵天将,八方游神,来我坛前听我号令。
“呜呼,呜呼,呜呼。”
我连吹三声号角后,边朝法坛打开坛手印,边掐着诀文念道:“一声号角起东方,竖起千山万仞坛。二声号角震天地,八方游神速来前。三声号角………吾奉杨师公法旨,开坛行法,急急如律令。”
开完坛,我便吩咐陈家人到院子外,将我事先写有陈真塘生辰八字、何处人士等信息的裱文,夹在纸钱里面一起烧掉,并且连放三串鞭炮,通告此方地境。随后,我脚踩罡步,手摇铃铛,一步一摇的绕着八仙桌连走三圈。等绕回法坛前,我字正腔圆的开始念起诀文,这一念就是半个多小时。
不管做大小法事,我最害怕的就是念诀文这个环节,枯燥又无味,但又无法跳过,诀文对一道法事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县里就有这样一位马虎法师,他前些年借玄天大帝庙宇做收斋法事,错把封神庵诀文,当做收斋诀文来念。结果可想而知,还没出两个礼拜,那法师就彻底疯了,三天两头光着屁股,在村里大喊大叫:“玄天大帝,哈哈哈,神通广大,玄天大帝。”
念完几万字送亡人诀文后,我按着酸痛的腰部,一拍法尺,朝法坛合掌拜道:“杨师公,弟子先行小憩半个时辰,坛中之事,请多多担待。”大多数法事进行到中场的时候,都能短暂歇息一下,这可不是我在偷奸耍滑。
接过陈家人递来的温茶,我吸溜几口后,便坐在靠背椅上闭目养神。不知过去多久,当我睁开惺忪睡眼,才发现自己竟然睡过头了。抬起头,此时月亮已上中天,先前大厅内悲痛欲绝的痛哭声,已经渐渐平息下来,偶尔还有几声凄厉的哭丧,依旧徘徊在深秋里的院落。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场生死离别,别开了阴阳两条路。
可能冥冥之中,杨师公自有安排。就在我起身时,无意间的往外一瞥,忽然望见院门外的村道上,静静地站着一名年轻女子。她背对着我,像个雕像般一动不动。我当时还诧异谁家姑娘这般胆大,三更半夜跑到这里来凑热闹。当我目光又往上挪动几分,才发现这年轻女子的颈部之上,竟然空空如也。如果不是细致观察,根本难以发觉,几乎同夜色融为一体。
真人在此,她居然还敢上陈家捣乱,这不是打我脸吗?有些火气的我,提起桌上铁剑,掐指下咒念道:“符行宝号,天师附法,起三昧真火,烧尽人间万邪……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我这把锈迹斑斑的法剑,是我祖辈传下,经过几代人温养,本身就具备一定法力,更别提它的前身还是柄杀生刃。若是寻常的鬼怪,我根本不用下三昧真火咒,单凭此剑就能将它们击伤击退。但很明显这无头女道行不浅,今晚我外有神兵天将护法,内有以斩妖除魔扬名的杨师公坐镇,她还敢在这附近游荡,足以说明来头不简单,至少是阴神级别。就在我踩着罡步,捏着法剑,杀气腾腾往院门外冲去之时,前刻还站在村道上的无头女,转眼之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常人见到鬼神,无非是运低、八字轻、机缘巧合,这三种情况造成,至于传闻中的阴阳眼,则属于八字轻中的一种。而法师见鬼,除了以上三种情况,还有就是神灵冥冥中助你见到,以及常年同阴阳界打交道,造成对阴阳之事的敏感。至于开天眼等等,只是影视的艺术化。不信的朋友,可以用牛眼泪擦眼睛就知道了,开天眼纯属无稽之谈。神鬼之事说来并不神秘,神秘的只是想要装神通的人罢了。
我虽然无法主动见到无头女,但这并不代表我拿她没辙。在法界有一种术法,叫做以位打形。民间也常用这法门去除晦气,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拿着棍棒、烧火钳等铁器,拍打鬼怪曾显形过的地方。这法门若是配合上相应的咒语手印,不但能去除晦气,还可以伤到鬼怪魂体。当然,这有时间上限制,牛鬼蛇神显形半柱香内最佳,过时术法威力就大减,甚至无效。
站在村道上,我将法剑重重插在无头女之前待过的地方。那时陈真塘村庄还没有通水泥路,只听嗤的一身,无锋的剑身顿时直接末柄。我沿着法剑的四个方位,各自打上一道手印。由于事先没有备下相应的符文,而此时再回法坛画符又比较耽误时间。我只好就地取材,从地上拔起三柱还在燃烧的清香,捏在手里,隔空画起神符。待入完尾部符咒后,我随即掐指念道:“二十七星宿归位(有一宿不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随法列在阵前。一请甲丁丙神开道,二请地听圣兽追凶……吾奉杨师公急急如律令。”
院内的几位陈家人,见我又是舞剑,又是比手画脚,一副神神叨叨的模样,赶忙跑到我边上。等我停下手中的动作后,陈真塘一位叔伯辈的老人,才小心翼翼问道:“师傅,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哪敢实话实说,那样我大师的脸面得往墙上挂。我清清嗓子,背着双手,颇有高人风范道:“没事,只是正常的法事流程,不需要担心。”说着,我指着插进地里的法剑,继续道:“家里有没有三年以上的大公鸡,有的话趁热取血,围着法剑倒一圈,记住撒的时候,要离法剑一米距离远。”
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加持术法的威力。三年以上的大公鸡血,已经属于纯阳之物,温热时比黑狗血,更具备驱邪的效果。我闾山派画某些符文,也经常用到大公鸡血。至于我为何不让陈家人,直接把鸡血倒在法剑上?那是因为正道法器,多多少少都怕沾染上众生血液,即便是大公鸡血也不例外。我家这柄法剑前身虽说是杀生仞,但自开道以来,就再没见过血光了。
回到院内,我一拍法尺,朝法坛一拜,继续先前未完的法事。治丧法事可分为前后两场,前半场基本上都在念诀文,极其枯燥乏味,冬天还好点,一到夏天简直就是蚊子的乐园。而后半场则明显生动多了,有过金银桥、敲阴阳瓦等桥段。
这里的金银桥,是座纸糊的假桥,长一米多点,宽约半米左右,一半涂成金色,一半涂成银色。做这道法事本意,是为了死者轮回路上好走些,少遭受点雷劈刀砍之苦。待陈家人将桥搬来,我一手摇着铃铛,一手执着法礼,大声念道:“此桥非凡桥,起自阴阳间,陈李林三奶坛前共作法,号得……吾奉杨师公急急如律令。”
烧掉一道开道符,我抓起法坛上的五色令旗,一把撒向金银桥,大喊一声“开桥”后,便提着写有陈真塘具体信息的红色小纸人,在两名熊腰虎背的中年男子一左一右搀扶下,小心翼翼的走上纸桥。由于纸桥的承受力很轻,我只敢用脚尖象征性接触一下桥面。这一米多长的路程,我几乎是被他们二人提着走完。过金银桥时,我本人就相当于陈真塘的亡魂,一旦桥面被踩踏,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轻则陈真塘亡魂不安,重则他会魂魄受损。除此之外,我本人还会折寿。这在法界叫做术法噬主,所以法师这碗饭,并不是那么好吃。
下了金银桥,我刚吩咐完陈家人把桥抬到院外去烧,大厅内便冲出一名貌美妇人。她拉着我手焦急道:“出事了,师傅出事了,我侄儿被我哥上身了。”
我认得眼前这美妇,她是陈真塘的妹妹,。父上子身,这是极少见到的怪事,我一时被勾起好奇心,忙安慰道:“不要着急,我跟你去看看。”
来到大厅,只见陈真塘儿子小陈,正瞪着双眼,杀气腾腾的在他爹棺材前,大打长拳,他边打还边大喘着粗气,仿佛在与人厮杀般。小陈今年也就十二三岁大,身材瘦瘦小小,但此刻他散发出来的力量,却大到出奇,居然连三名成年妇女合力都制不住。其中一名不知是他姑姑,还是他婶婶的壮妇,被他反手一推,一脚绊翻了烧纸钱的火盆,顿时黑色纸灰飘散的到处都是,把庄严肃穆的灵堂,闹得不成模样。
这时,从里屋走出一名头戴白花,双眼通红的女子。她推开众人,抱着小陈嚎啕大哭道:“死鬼呀,你走就走了,干嘛要来祸害咱家的儿子。”
我打量小陈一眼,道:“表嫂,他不是表哥。”(陈真塘是我远房表哥。)
陈真塘妻子一脸茫然的问道:“那他是谁?无头女吗?”说到这里,她连忙将小陈推开,跑到我跟前,用力拉着我衣角,央求道:“表弟,快为你表哥报仇,快为你表哥报仇。”
只听扑通一声,前刻还在打拳的小陈,突然一个后跳,离地而起,四平八稳的坐在还未合紧的棺材板上,伸手向人要起烟茶。我虽然隐隐约约猜到他的来历,不是将公就是帅爷。但出于气他搅我法场,不给我林某人面子。当下我也不管他是正是邪,双指左勾右绕,急急甩出一道手印。
“天地正法,源自正心。八卦灵灵,脚踩七星。上驱妖神,下诛邪灵……吾奉玉帝法旨,急急如律令,退。”
我刚念完此咒,小陈身体便为之一震。他皱着眉头,念了几声法号后,居然也开始打起手印,他这手印不是朝我打,而是朝他自己身上打。不言而喻,他这是在解我下得法术。我这法下的不重,只是逼他退身,因此他很快就破法而出,高声唱道:“吾乃安西铁将军,入得闽境安民乱。丈八陌刀扬国威,一腔忠心是赤胆。未上凌云……”他边自报家门的同时,边用指关节叩击着棺材板,一句一调的和着节拍。
眼见厅门外面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我没功夫听他那些英雄事迹,一执法礼,打断他道:“先前还以为是妖神作乱,殊不知是将军降临,多有得罪,请多包涵。”我递上一支烟,继续道:“我乃闾山师法主杨师公座下弟子,请问将军如何称呼?”
他没有回我,只是重重的冷哼一声。由于他前刻已经自报家门了,我这时候不敢再驱法强催他下身。只好打起感情牌,道:“今晚陈家治丧,将军有何事,能否过了今晚再谈,毕竟死者为大。”
他视若无闻,又是一声冷哼。我无奈之下,只好请杨师公上身劝他。正神强行上身,处理起来就是如此麻烦,你使法驱他,不合天道,可能会遭反噬。你不使法驱他,他又赖着不走。心中默念杨师公神讳,还没片刻功夫,我顿感一阵头重脚轻。等胸口那暖暖的温热劲头过后,我便失去七分意识了。
请神上身,并不是完全失去意识,这得看请何方神灵。迷迷糊糊中,我有听见杨师公借我之口劝他道:“杨都公元帅,请速速下身。老道我术法无眼,别伤及无辜。”
上小陈身的杨都公元帅,按神祇排名,跟师法主杨师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至于神通方面,更是有着云泥之别,一个擅长看家护院,一个精通行坛布法。不过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听从杨师公的威胁,自行退身,而是娓娓道起跟陈家之间的恩怨纠缠,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那般,倾吐着苦水。
杨元帅与陈家之间的故事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陈家的祖辈。由于当年陈家连续几年非祸即灾,便找法师到庙里请杨元帅坐镇家宅,作为保家神世代供奉。保家神多数就是这样流传下来,还有一部分是因福缘主动寻到你家中。百年来陈家人一直都有供奉杨元帅香火,到了陈真塘这两代,因为他们父子二人都不怎么迷信鬼神之事,也就不再供奉了。
若是不想供奉保家神,那必须要找法师把他送走,好聚好散,否则会遭反噬,特别是民间百姓常供奉的阴邪神。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经常风闻某某家信基督教后,妻离子散。这不是我故意诋毁基督教,而是那些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没处理好保家神的问题,才造成的后果。
杨元帅是地境正神,生前嫉恶如仇,经常替人打抱不平。他与黑面将军一样,都是因愚忠而死。化羽成神后,他生前刚烈的秉性,只增不减。按照常理而言,即便是陈家人不供奉他,他也会保一方平安。无头女道行虽不浅,但在他面前,就好比螳螂斗公鸡,小菜一碟。
不过坏就坏在,陈真塘妻子在亲眼目睹无头女显形之前,根本就不相信神神鬼鬼之事,天生就排斥迷信行为。她嫌杨元帅的裱文、香炉搁在大厅太碍眼,就把他们全部整理到快倒塌的老宅。而那栋阴暗潮湿的老宅,夏天进雨,冬天漏风,里边还圈养着成群的鸡鸭牲畜,臭气冲人,人待着都受不住,更何况神了。
杨元帅一代正神,落到这般境地,也算是他修行路上的一劫。他下身前,曾指着陈真塘妻子,怒目圆睁道:“陈白花阎口虽见血光,不过还有一线生机。若不是你无知愚昧,在本座庇护下,他本不该死,至多也就落个残身。”保家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帮供奉他的人挡劫煞,当然必死的劫煞,他们也挡不掉。天道轮回,有生有死,谁也无法扭转。
等杨师公与杨元帅一起退身后,精疲力尽的小陈被陈家人扶回里屋休息,我见厅中无事了,便回到院中,趁着时辰未过,摇起铃铛,开始最后一道敲阴阳瓦的法事。敲阴阳瓦这道法事,一共需要七片青瓦,每片青瓦代表着阴间一重险关。这七片青瓦正面,还画有一道用朱砂为颜料书写的送阴人符。我把青瓦用砖头垫起来,一片连着一片,向着大厅棺材位置,摆成北斗七星形状,掐指念道:“过刀山,看望乡,一路难来一路关……弟郎号角从天落,三拜恭迎陈大奶……宣封临水夫人急急如律令。”陈大奶是闾山法主陈靖姑的俗称,她下阴本领很高,与阴间一众神灵交情比较好,所以治丧法事经常需要请到她尊驾,遣她同亡魂一起到阴曹地府报告。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不但能适用于阳间,阴间也是如此,世上本来就没有净土,只是世人对美好的一厢情愿。
颂咒毕,我烧掉一道遣阴司符,对着列在地上的青瓦,再次掐指念道:“起阴司令,头戴三冠,手拽法链……令到三更鼓,速到坛前听调……一更鼓起,二更鼓起,三更鼓起……阴兵阴将,列在坛前,奉师法主杨师公法旨,急急如律令。”
由于出外做法事携带鼓锣不方便,我万事从简,以鞭炮代替法事上的更鼓,每催一道更鼓,就让陈家人放一串鞭炮。连续催完三更鼓,我提着刚从院外拔起的法剑,站在青瓦北斗阵边上,手起剑落,一剑一片青瓦。当所有青瓦全被我敲碎成龟裂状,我便叫陈家人点着贴有引路符的白色灯笼,并大烧纸钱。随后,我朝天地各三拜,一执法礼念道:“闾山师法主杨师公门下弟子林白花,遥拜地府真君、地藏王菩萨……闽地XX人士陈真塘,父XX,母XX,生于XX年,故于XX年……”
做完这道法事章程,这场治丧法事基本到达尾声了,余下全是些念诀文烧纸钱等枯燥环节。我是第一次在治丧法事上,遇到这么多风波,本以为这场法事不可能顺顺利利。当我收坛时,习惯性摔阴阳杯问杨师公法事进程,结果却是三问三正负(一阴一阳),出奇的顺利。
回到家里的当晚,我一前一后共做了两场梦。第一场梦是梦见我家厅中的靠椅上,正大马金刀的坐着一位蓬头垢面的元帅,他模样虽说狼狈,却丝毫不减当年的威风。他在我家待了片刻,便朝厅一位穿着古装的老道抱拳走了。第二场梦是梦见一位无头女,鲜血淋漓的倒在一处山沟下,边上还围着几名拿着刀棍链条的兵丁,朝她大凶嚷嚷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古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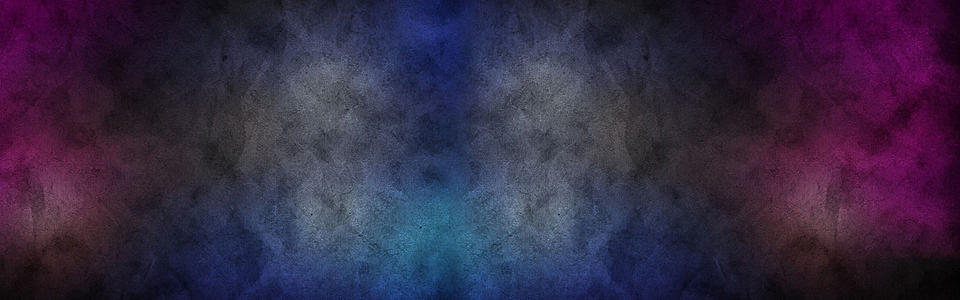


写这么多,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阿弥陀佛
写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