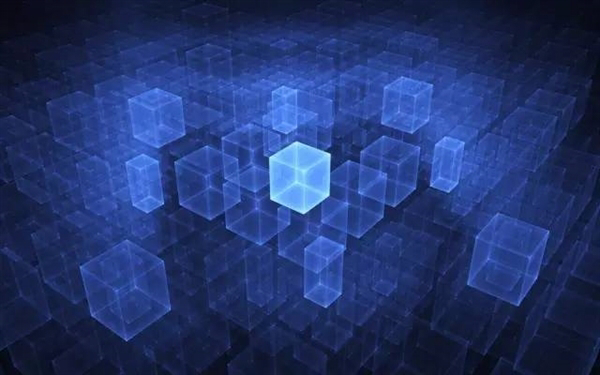这是我全程经历的故事。一个同学兼好朋友,就叫他阿广吧,阿广两夫妻在小县城开个夜宵店,平常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虽然辛苦一点,但小日子还算可以。
阿广的父亲早去世,母亲在乡下跟大哥生活。今年五月,阿广的母亲病了,加上年纪也不小,一病就躺床了,吃喝拉撒都要人侍候着,他大哥两夫妻也是打工之人,难以抽身,于是两兄弟商量,反正阿广是开夜宵店的,白天就由他侍候母亲,晚上大哥放工后就由大哥接班,阿广再赶回县城的夜宵店开工。
他乡下离县城不远,也就七八公里,但中间隔着一座山坳。这天晚上,阿广有几个同村的兄弟外面打工回来,晚饭时一起喝了两杯,到了11点多了,酒气才消了,阿广想着老婆一个人在夜宵店怕是忙坏了,于是开着摩托车要回县城,兄弟们都说这么晚了,干脆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再走吧,阿广想着一来老婆那边忙不过来,二来明天白天又要侍候母亲,一留下来就要到明天晚上才能走了,还是连夜回去的好,就开着车走了。
午夜的乡下非常宁静,一路只有摩托车的声音和昏黄的灯光穿过窄窄的山路,两旁是密密的竹林,初夏的五月不时有虫子的叫声。走了两公里左右的上坡路,到了半山坳,再转个弯下个坡就是县城公路了,这个山路阿广从小到大不知道走了多少回,只不过以前是自行车走泥路,现在是水泥路可以走机动车了。
就在阿广的车子转到半山坳的时候,“咔”一声,摩托车熄火了,阿广嘴里暗骂这烂摩托,关键时刻总是不争气。下了车,架起车子,一下一下打火,就是打不着,用脚踩也打不着,真没办法,阿广彻底失望了,停下手脚,刚才一轮动作,搞到一头大汗,他看一下四周,虽说是初夏的夜,突然觉得山中的午夜还是透着一阵阵的凉意,他叹一口气,唉,看来天要留我住一晚了,还是回头吧,好在回头的路都是下坡路,阿广开着车灯,心想大不了明天换个电池,就慢慢遛车回到村子,他那几个兄弟还没睡,见他倒回来问清是什么事就拿他开玩笑,有一个说我看看,怎么就打不着火了?
用脚踩几下,呼的一声,打着了。大家就哈哈大笑,说阿广啊,你是不是撞什么邪了?阿广想着反正都倒回来了,不走了,就发了个短信给老婆,在家里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阿广就觉得浑身重重,喉咙不舒服,头沉沉的,他想肯定是感冒了,不禁感叹自己这段时间又要兼顾生意又要侍候母亲,熬坏了身子,于是到村边采了些鱼腥草、茅草叶等平常用的草药熬了一锅水,喝了两碗,剩下的趁热冲了个药水凉,乡下人对于感冒发烧都有自己的土办法。这一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好不容易等到大哥放工回来,晚上六点多的时候,阿广说看来感冒好象越来越重了,我要回县城看看医生了。回到县城,就是小区门口的门诊叫医生把了个脉,拿了两天的感冒药,无非感冒灵之类的。至于母亲那边,阿广就叫老婆这几天夜宵店暂时不开了,代替自己每天回乡下,他自己就先把感冒养好。
阿广的老婆如是天天跑回乡下,晚上就回来,开头的几天回来总是看到阿广软软的躺在床上,问有没看医生,有没有好一点,阿广总是说:看了,差不多。每次问都是这样回答。如此又过了四五天,他老婆有点耐不住了,怎么感冒都这么难搞,莫不是有其他病吧?就拉着他到县人民医院找了个相熟的医生帮看一下,医生说既然感冒这么多天不见好,干脆做个检查吧,什么血糖、肝功能等都作了检查,数据显示又没什么事,问阿广什么感觉,阿广就说累,也没什么胃口,浑身没力,坐都坐不稳的样子,就是想躺着。医生就开了几天吊瓶,老婆天天用摩托载着他跑医院吊瓶,因为阿广总是说累,所以每次吊瓶都开个床位躺着吊,乡下的老母亲只能让他大嫂请假在家侍候着了。如此又过了四五天,还是不见有好转,从发病开始有十多天了。
这天,我回到县城,到一个叫阿源的朋友的农庄喝茶,这个阿源跟阿广也是非常要好的,阿广开夜宵店之前就在阿源的农庄当厨师,只要我回县城,总是要到阿源那里坐一下,也经常叫上阿广一起吃个饭喝个酒的。跟阿源喝着茶,自然问起阿广(因为阿广做夜宵的,到凌晨四五点才收档休息,一般我们中午之前是不敢打扰他休息的),阿源说阿广的母亲最近病了,他要两头跑,够累的了,这些天都没怎么联系,等中午饭的时候给个电话他一起吃个饭吧。到了中午十二点多,我打阿广的电话,电话那头软绵绵的声音,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告诉他,我在阿源那里,如果有空,中午一起吃个饭吧,他倒是一如既往的爽快,说既是老同学回来了,怎么都要见个面的。过了一会,阿广的老婆载着阿广来了,一见面,我和阿源都大吓一跳,这什么人啊?只见阿广人瘦了一圈,面色腊黄,双眼无神,走路都不稳的样子,寒喧一番之后我问:阿广你怎么搞的,感冒也这样胡弄人?是不是血糖高啊?他老婆说:刚检查了,什么指标都没事。阿源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也不怕说了,是不是伤寒夹色(就是男人感冒、伤寒或大病期间过性生活,民间传说这样男人会大伤元气,甚至性命不保)。他老婆说:没有,真的没有,这段时间他忙着侍候母亲,我顾着大排档,哪有这门子心思。接下来的饭局阿广只喝了一小碗的汤,根本没吃东西,吃完了我们就叫他两夫妻早点回去休息吧,继续看医生,先把身体养好,大排档就先关着门吧。
又过了三天,我想着不知道阿广会不会好一点呢,就打电话过去,没听,到了中午再打一次,他老婆接了,我问阿广怎么样?好点没有??她说还是这样,唉,都看半个月的医生了,检查也没什么状况,就是没力气,整天的睡,电话都不想接了。我就叮嘱一番,说再找其他的医生看一下,也或者找中医看了可以。我还介绍了一个相熟的老中医,让她带阿广去看一下,毕竟这样拖着不行啊。挂断电话后,我又打给阿源,说起阿广,阿源也摇头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感冒就搞得不象人样了?接着他说了一句:会不会是碰上那个东西了?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东西是指非阳间的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向来是不承认其有,也不反对别人相信,很多时候,人都是为了求得心安理得。于是我就说,既然看这么久医生还不见好,总不能这样下去吧,你看有没有相熟的大师之类的,帮一下他吧。阿源说,你是他老同学,你向他说一下看看,相熟的大师有认识的啊,如果真的是碰到那东西,关键是阿广要配合。于是我再打电话给阿广,这次是他接了,我将意思跟他说了一下,想不到阿广非常明确地说:没有,不会的,肯定不会碰到这东西。我说:这东西我们又看不见,你就见一下大师,让看一下吧。他非常强硬地回答:不用,没有。那种强硬的态度是我这个二十多年的老同学从来没见过的。我将情况跟阿源说了,阿源说:既然这样,从他老婆那里了解一下看看。我发信息给阿广老婆,让她方便给个电话我。到了下午,阿广老婆打电话来,我将我和阿源的想法说了一下,问她阿广这段时间有什么反常没有,她说其他倒没什么,就是半夜老说梦话,又听不清楚说什么,叫醒后问他,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他以前是不说梦话的。我叫她去找阿源,大家商量一下看怎么处理这件事,都病有二十多天了。
阿广老婆找到阿源,因为我跟阿源早通气了,所以直入话题,阿源说帮约大师见个面,考虑到阿广的抗拒情绪,叫阿广老婆想办法以喝茶吃饭的形式把他拉出来,让大师面对面看一下,为了让阿广没借口推却,阿源叫我也回一趟,一起约阿广出来。为了老同学,我当然没二话了,这天中午,我们约了阿广在农庄吃饭,阿广开始说累,只想睡觉,不想出来,他老婆说:你老学跑一百多公里专程回来看你,你就坐一下吧,没胃口喝个汤也行啊。拉着他出门,到了小区门口,阿广看见猛烈的太阳(六月初了,南方的天气好热了)又说不想去,想在家睡觉。他老婆不让他回,硬把他按在摩托车上载他过来。
大师是一个相貌平凡的中年人,坐在席间就说是我那边的朋友,一起过来办点事的,阿广依然是那副模样,只是脸色更难看了,象黄泥水的颜色,依然没胃口,也是只喝了点汤。整个吃饭过程我们只是拉拉家常,阿广坐一会又说累,我们就说嫂子先载他回去吧,回来见个面就很不错了,让阿广回家好好休息。他两夫妻走后,阿源问大师:怎么样?大师说:是,上身了。阿源问:是什么鬼?大师说:他的本家兄弟,在下面孤单,想让阿广下去陪他。大师问:有十几天了吧?阿源说:听他说五月十日左右,应该有二十天左右了。大师沉吟了一阵,说:嗯,要处理了,再这样下去,不出一个星期,你的朋友小命不保了。我问:这么厉害?大师说:阴间以七为算,你朋友让鬼上身二十多天了,算起来就是三七了,过得三七这个坎,难保能过四七,你看你朋友这气色,水都喝不多,没一点力气,元气不多了,再不处理,必死无异。大师接着说:刚才吃饭期间他离开了一会,就是跟这个鬼通了灵,问清楚了前因后果,这个鬼是阿广的亲兄弟,早死,就葬在阿广乡下的后山,那天阿广半夜赶回县城摩托半路熄火,就是它作的祟,它在下面孤苦伶仃,想拉兄弟下去作伴。阿源说:不可能吧,阿广就两兄弟,一个大哥在乡下,没听说他有其他兄弟啊。大师说:可能年代久远了,只有问他母亲才清楚。阿源问:那怎么处理呢?大师说:我刚才跟那个小鬼说了,说它再怎么也不能害自己亲兄弟啊,让它放手吧,它似乎有点惭愧,我们再烧点东西送送它应该可以搞定的。阿源拿出个红包递给大师,大师也不推搪,转身从挂包里拿出纸笔,用黄纸画了符,再用另一张纸列了一些东西,说:符烧了化灰冲水喝,买齐那些东西晚上十一点到那天摩托熄火的地方烧了拜一下,拜完就走,不要回头看。我和阿源多谢后送走大师,因为我要回程赶路,就叮嘱阿源一定要把事情办妥。
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阿源问情况,阿源慢慢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见大师的那天晚上他有事,没去处理,但跟阿广的老婆跟电话说了,他老婆说阿广现在喝水都懒了,这符水怎么喝啊?再说他一再反感我们查神问鬼,如果明知是符水,打死他也不会喝的。阿源就帮她想办法,说阿广喜欢喝普洱茶,你就说朋友见他不舒服,送了一个上等茶饼探病,泡一壶浓浓的普洱茶,然后把符化在茶水里,他喝了也不知道。阿广的老婆第二天清早就去阿源处拿了符又去香烛店和市场买了大师叫备齐的东西。回到家里按阿源的吩咐依法炮制,阿广真的就喝下去了,还说这茶色还可以,但茶味淡口(喝什么都没味道啦)。喝完后又倒身睡觉,睡到下午四点多才醒,阿广坐在床上,让老婆拿水给他喝,突然说了一句:好象有点肚子饿了,有什么好吃的吗?他老婆喜出望外,这十几二十天都没见他说过肚子饿的,连忙去煮了点瘦肉粥,阿广吃了半碗,又不想吃了,说想起来坐坐,老婆扶他坐在沙发上,帮他开了电视。跑到卫生间打电话给阿源,说:阿广讨东西吃了,好象有点效果了,但那些东西要在半夜十一点去烧拜,她一个女人不敢去哦。阿源说我陪你一起去吧,不要怕,今晚就去。
到了晚上十点多,阿广老婆就说,看你今天精神点了,今晚一个外地的亲戚回来了,明天就走,约去见个面,就在小区门口的大排档,坐一会,让阿广先睡了。出了小区,阿源已经在门口等着,两人共乘一辆摩托车,向阿广乡下方向出发。虽说是白天车来车往的公路,但到了十点钟后,基本已没什么人了,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那个小山坳,阿广的老婆平时出出入入这条路都习惯了,从不知道什么是怕,但今天晚上要办这种事,而且毕竟是女人,她紧张到拉着阿源的衣服大气都不敢出,阿源自诩是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不怕。这天大约是农历初十前后,月亮还不是很明,朦胧的光让人有种恐怖感,四周不时有些夜鸟叫声,更让人一身皮肤不由得一阵一阵发紧。两人借用手机电筒的亮光在路边找了一块稍平坦的地方,将生猪肉、苹果、米饭、香烛纸钱等东西摆好,点起香烛,用纸杯倒了三杯酒,烧起纸钱,边烧边拜,阿源朗声说:陈家兄弟,现你的兄弟阿广特设生肉果品拜祭你,希望你念在兄弟的份上,从此不要打扰他,这份香烛纸钱送你离开,以后各自营生,你也一路顺水。说完奠上三杯酒,把米饭抓起向四周洒开。说也奇怪,这时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卷起一阵阵纸灰,阿源拉着阿广的老婆掉头上了摩托就走。回到家里,阿广还在看电视,精神看来好多了。
又过了三天,刚好是周末,因为在电话里听阿源说了整个事情,我又跑回小县城,想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显效。还是在农庄,还是阿广两夫妻一起来,阿广看起来好多了,虽然脸色还是不太好,但总算有点精神了,吃半碗饭,还吃几块鸡肉,我笑着逗他要不要喝两杯酒,阿源说还不行,禁酒一个月。我们几个想着反正事情过去了,就把请大师然后送鬼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阿广听得瞪大眼睛一脸茫然。我说:之前我问过你会不会是碰上脏东西了,你拼命说没有没有,还记得吧?他说:你什么时候问过我这问题啊?他老婆说:那你说梦话,醒了之后我问你的东西呢?阿广还是一脸茫然,一副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后来说起这东西是他的亲兄弟,他说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兄弟,改天回家问一下母亲。
再过了二十多天,这天我给电话阿广,他只说了一句:在乡下,很忙,过两天再复我。就挂断了,我打电话给阿源,阿源说阿广的母亲去世了,正在乡下办事呢,而且母亲临死前说了,阿广之前有一个大哥,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生育医疗条件,发生孩子夭折的事虽不说司空见惯,但也确实是常有之事),当时就在后山刨个坑埋了。
再过了一个月,阿广的大孝出了服,酒也开禁了,我专门拿了瓶洋酒回去,跟他喝了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