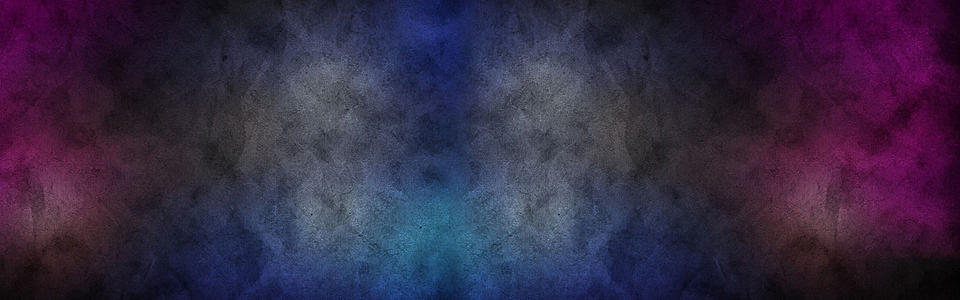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工作的时候操作不当,不小心割伤了。”
他笑着看着我说道。
“看起来很疼的样子。”我说。
包扎的绷带上,还有渗出来的一点血迹。
“缝了二十针而已,没事的。”
他举起手臂对我说,但用力过猛,伤口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咧嘴。
我俩相视,都笑了。
那次离开医院之后,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我经营着一家早餐店,每天凌晨三点半便要起床准备。和面、醒面、剁菜、和陷,然后再灵巧的包成小笼包,上蒸笼十五分钟,一屉屉漫着肉香的包子便可以出炉了。皮包陷厚。若是用筷子将小笼包夹起来,是一个完美的水滴状,面皮微微透光,可以隐约看到里面的肉馅。咬一小口,鲜美的汤汁便一涌而出,若不仔细会烫着嘴。肉馅是新鲜的猪里脊,配上猪油粒、大蒜末、葱花、马蹄爽,等等一些辅料,口干绵密又富有层次感。五年来,一直是店里的主打产品。
这是我母亲的配方,小时候每当我生病的时候,她就会做给我吃。
我的整个童年,都弥漫着这样的味道。
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母亲围着围裙的背影,在简陋的厨房中,一边哼着曲一边在厨房中包小笼包的场景。
很香。
“这是什么配方?”
他第一次来我店里,吃了一口小笼包之后,满脸惊喜的问道。
我笑着摇摇头,说道:“秘密。”
他也笑了,一只手夹着包子不停的往嘴里塞,一只手吊在胸前。
“怎么了?”我问起关于手臂的事情。
“摔倒了。”他说。
“真是冒失鬼,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
他笑起来很好看,很像是我小时候电视机里的一个主持人。
不记得那个主持人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生病在家的时候,母亲会把电视机打开给我看。
电视机是一台老式的彩电,遥控器的后盖掉了,电池总是松脱,所以被遗弃在了茶几底下的某个地方。
不是,或许是沙发的下面。
不记得了。
总之,如果要换台需要起身,然后打开电视机屏幕下的一个小盖子,伸手进去按一个黄豆大小的按键才可以换台。时间久了,按键也磨损的厉害。必须在按下去的时候,用一点力才可以。很麻烦。
所以,电视机打开之后我就会躺在沙发上一直看。无论播放什么节目,都不换台。
大约是下午的时候,母亲哼着曲在厨房做小笼包,电视机里会播放一个儿童节目。想不起节目的名字了,只记得有一个绿色的玩偶,还有一个主持人。每当镜头对着这位主持人的时候,他都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浓眉大眼,牙齿很白,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我好像也看过这个节目。”他说。“好像是下午四点的样子,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
他又不好意思的笑了,但又立刻按住了腹部,表情有些痛苦。
“没事吧?”我问。
“没事没事,过医生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
“我也曾经得过急性胃溃疡呢。”我说。
虽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似乎只有这样的事情——小时候看过同样的节目、曾经得过同样的疾病,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
六月的时候,我和他同居了。
一向冷清的单人公寓,忽然多了许多陌生的物品,让原本拥挤的房间变得更加局促。但是我不介意,反而觉得空间的狭小让我们的距离更近了。
衣橱里多了三分之一的衣物,餐桌上多了马克杯,鞋架上多了几双鞋,书架上多了书籍和一些药瓶,茶几上多了许多我没吃过的零食,床上多了一个枕头。
这些改变,令人欣喜。
“这些全部都要吃吗?”
“不用,”他拿起一粒白色的药丸,用汤服下,说道:“饭后吃这个就可以了。”
胃病早就好了,但是肠道又出现了不适。似乎很正常,肠胃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日子过得不紧不慢。我依然每天三点半起床,他在六点离开家去上班,中午的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餐。
平静而安逸。
直到一天早晨,我一如既往的重复着手里的工作。一个男人忽然出现在了面前,先是对我的手艺赞扬了一番,然后提出希望可以帮我开一家分店。
我有些惊讶,喜悦又有顾虑。
“但是需要将配方教授给分店厨师。”那个男人说。
我犹豫了。
这是母亲的配方,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能与人分享的。
“啊,医生说可能需要动手术也说不定。”
他忽然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
“突然严重了吗?”
“嗯。”他说:“拿到的CT结果,好像有一些异样。”
因为这样的事情,几年来第一次,我没有在凌晨三点半起床。
闹钟响了之后,我悄悄关了。转身又依偎在了他的身旁,他睡觉的样子我也喜欢。我伸手轻轻抱住了他的腰。他赤裸着上身,呼吸均匀的睡着。
我仔细看着他随着呼吸起落的腹部,缠着纱布。
昨晚为他换药和清洁手术伤口的时候,但看着实在令人心疼。
我决定了,拒绝了开分店的计划。
“今天一起去什么地方吧。”
早餐的时候我对他说:“公园,电影院,或者是动物园。怎么样?”
他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肩,吻了我额头。
“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他在我耳边说道。
好久都没有来过动物园了。
上一次,好像是和母亲一起去的。
是在一次生病之后,母亲带着我去了一家动物园。说是动物园,但是其实并没有多少动物。是一个资金有问题、即将面临倒闭的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寥寥无几,剩下的也只有两眼无神的猴子、奄奄一息的狐狸、有气无力的河马和终日垂头丧气的长颈鹿,唯一的卖点是一头骨瘦嶙峋的狮子。
对于那个动物园,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它的建筑。
关闭了的海洋馆外,有一个一层楼左右高的阶梯。白色的阶梯,在太阳下让人眼晕。稍不小心,便很容易眼花而滚落下去。
好像有过这样的新闻,有一个孩子从那个台阶上跌倒,滚下去了。
想到这里,我忽然有些头晕。
“没事吧?”他扶住了我。
我低头,发现自己走在一段阶梯上。一只脚正踏在台阶上,另一只脚的脚腕无力的歪斜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台阶,太多了。”我说。
我仔细的低着头,慢慢的下台阶。几乎要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些台阶之上。有人说话,有人从身边经过,都不能可以让自己分心。
一定要注意每一步,我不停的在心中念叨着。不自觉地,我将身体的重心后移。
真不应该穿这双新鞋,不应该追求什么线条美,平底鞋才应该是最好的。我懊悔的想到,鞋跟太细了。
万一鞋跟断了怎么办?
万一没有踩稳怎么办?
万一又崴脚了怎么办?
万一有人从背后推了我,怎么办?
会摔下去的,一定会摔下去的。
会很痛。非常的痛。
我这样想着,仔细脚下的每一步。
一个灰白色的东西忽然从我身边滚落,我立刻停下了脚步。
是一个人。
我顾不上脚上的鞋了,慌忙的跑了下去。
早上为他选的白色衬衫,一侧有红色的斑点,像是还没绽放的玫瑰花苞。
“是不是很痛?”
我看着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握着他的手问道。
因为头部和脖子都被固定了,他只能微微的对我笑了一下。
我将自己的头靠在他的手背上。
“你说会不会是我们的八字不合?”我说。
八字不合。听起来很迷信。
但这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似乎母亲也对我说过。但具体是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也想不起来了。
他否定了我的想法,但现实却是,他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日子慢慢又恢复到了往日,这个房间又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经营的早餐店,上午是一天之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要稍微差一点,毕竟我只会做小笼包,早上吃过的客人中午很少再出现了。下午两点便关门休息,然后去市场买好第二天要用的食材。
今天中午,我没有接他打来的电话。
吃过晚饭之后,闲来无事,我开始收拾和整理他的东西。
“不要这样,我不想离开你。”他给我发来了信息。
我没有理会,将手机放在一旁。
他的东西不多,一些衣物、几件器皿、几本书籍、一些琐碎的小物品,还有一个旅行箱。
手机屏幕偶尔还会亮起,跳出信息显示。
我将旅行箱打开了,里面还有东西。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得东西。
是几个牛皮纸袋的文件袋,有大有小。
我将最大的一个打开,是一张腹部CT。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再打开一些小的文件袋,都是一些医院病历和体检报告。
他向来身体就不好,是在遇见我之前的事情。
我忽然有些难过,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了。”
我这样回复了他的信息。
我将这些病历资料装回了文件袋,打算关上箱子的时候,发现在隔袋中有一个硬物。
是一张光碟。
虽然不应该偷窥他人的隐私,但是光碟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好奇。
我打开了电脑,播放了光碟。
里面出现了一个人,是他。
他拿着一把刀,对这镜头哭泣着述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他在嘴里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不断地哀求她不要离开。
我看着屏幕里的他,感觉胸口有些刺痛。
“如果你离开我,我就去死。”
屏幕中他这样说道,然后狠狠的朝自己的手臂划了一道。
鲜红的鲜血瞬间溢出,像红色的玫瑰花,开满了他衬衫的袖子,又蔓延到了腿上,最后落在了地上。
我看到了屏幕上显示的拍摄时间。
这么深的伤口,估计要缝二十针。
我合上了电脑,立刻将那些收好的文件袋又打开了。
几份体检报告,机打的各项检查结果,均为“良好”。
几本医院病历,却写满了各种疾病。胃溃疡、慢性肝功能衰竭、肠道良性肿瘤、心肌缺血,等等。
日期一直到最近几个月。是他的字迹。
我打开最后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手术同意书。
认真阅读的话,有几个谐音错别字。
我拿起了手机,找到了这份手术同意书的医院电话,以家属的身份简单询问了几句。
并没有他的手术记录。
我挂了电话,忽然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喂?”我接了。
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语气兴奋。
“还是算了吧。”我打断他说道。
电话那头先是沉默了一阵。
良久,终于有了声音。
“听医生说,脚上的伤太严重了。”他说:“可能需要截肢。”
几天后,我将他的东西寄回了他父母的家中,再次过起了原来的生活。
忽然觉得,家里的空间好像变大了。
母亲死了之后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不再用的东西清理掉了,家里的空间似乎就会变大一些。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和面、醒面、剁菜、和陷,然后再灵巧的包成小笼包,上蒸笼十五分钟。整个店里,开始弥漫着香气。
每天如此。
不同的是,马路对面总站着一个人,微笑的看着我。
这个人,笑起来很好看。
杵着拐,没有右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