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常常和弟弟在这条路上散步,路的尽头是小镇集市,每次,我都会买些糖果给他,可是他在乎的不只这些。
每次的散步,他都会指着路边的那些树木、花草问我它们的名字,于是,我就会告诉他,并给他讲松树傲然风雪的故事,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萋萋青草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
于是,每个周末,跟我去散步,听我讲故事,都成了他的乐趣,而我的任务便是在业余时间多读些书,好在这样美好的时刻讲给他那些传说、故事与童话。
他是份外聪明的,我每回讲给他的故事,他都能一一记得,并且讲给邻居小伙伴听,回来时,就一脸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多么的崇拜他。
记得他小时候,我牵着他的手走在这条小路上,那是他第一次跟我来散步,他很小心地问我,哥哥,你会迷路吗?
我笑着摇摇头,反问他,万一你迷了路怎么办?找得到家吗?
他说,我找不着,可是,我会在原路等你,你一定会找到我的。
多么聪明的弟弟,现在想想,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可是想到他那天真的样子,也不禁让人怜爱。
现在,我就站在当年给他讲过的那棵松树的旁边,松树变高,变壮了,却依然昂着头望着天边那片浮云,似在追忆往事,就像我这样,看着曾布满我们脚印的土地,不禁想的两眼朦胧。
这条路,这些草木依旧,可是,来散步的人却只有我,而我的弟弟,浔,却离开了我,永远都不能再与我在这条乡间的小路上散步,并抬起天真的脸孔与我说话,他死了。
他死在自己的住处,今年二十岁的他正在念大学,成绩卓越,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懂读书,他的死让人很意外,也很不可思议。
不是情杀,因为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喜欢的女孩,虽然校园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可是他一个也没有喜欢的,他只喜欢学习,也许是当年我给他的影响。
他曾说过,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个学识渊博的人,知道那么多东西,所以他也要向我一样,读万卷书。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事,对于他过于浓重的书生气,父母曾一度发愁,可是他依然沉浸在书海里不可自拨。
可是,就这样一个学校、住处两点一线的孩子,为什么会有人登堂入室地将他杀死了呢?
他死的很惨,先是被人用钝器击中后脑,然后用尖刀连刺数下,其实,在被击中后脑时他就已经死了,又有谁与他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
警察已经调查好几天了,除了抓过一个跟他在学校吵过几句嘴的同学,后经核实没有在场证据而放掉外,再无任何进展。
更奇怪的是,警察们说在屋里没有任何线索,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衣服纤维,没有毛发,并且不是劫财,他的信用卡,现金都没有少。
就连邻居也说在听到一声惨叫前都没有任何声音,这是个怎么样的杀人者啊,是有预谋的吗?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残忍的去伤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良的孩子?
若说,浔是生病去逝,也倒能让人接受,可是他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换成谁也是不能释怀。
父母自得到消息后就一直住院,姑姑姨姨们也都想起就掉泪,我一向不在人前流泪,只好走到这小路上来,所到之处,似乎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手心里,似乎还有他的温暖小手的温度,可是,低头看看,只有黄土和被风吹起的枯叶。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家里的气氛依然惨淡,父母出院了,还是吃不好。
案子没有结束,我们将尸体送去火化,他躺在水晶棺里衣冠楚楚,轻轻瞌着的双眼,似乎随时都能张开,微微闭着的双唇也似乎马上就会露出洁白的牙齿对我微笑。
但是我明白,不能了,一切只能在梦中想象。
最终,他还是被送入那个燃烧的大炉,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血肉化成了缕缕青烟,消失在乌云密布的天空。
浔,你就这样走了吗?不再叫最后一声哥哥,不看我,不再对我微笑,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讲给你听,你还听吗?
浔离开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没有笑声,甚至没有人说话,三人之家成了无人之所,若不是进来,在屋外根本不会知道,这个房子里还会有人在。
可是,日子还要继续下去,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我只能站起来,扶着父母继续前行啊,没有了浔,还有我,还有我。
开始我几乎天天去警察局,后来我发现,只要我去,晚上就会做恶梦,梦见浔血淋淋地站在窗外,一言不发,双眼充满哀怨。
醒来,都是一身冷汗,后来,我隔三差五的去,以后就是一个月去不了三四次,案子就这样拖着。
我回到社里上班,别的人都很敬畏地看着我,因为我心情不好,很糟糕,以前我从来不把情绪带进工作区,现在我没有办法做到。
桌上有我跟浔的照片,看着他的笑容,我就会沉进无限的哀伤里去,然后就是无名的烦燥,想对任何人大喊大叫,工作效率也直线下降。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副主编,我想我早就被炒掉了,于是主编让我放大假,我回绝了,我承认是自己的情绪太偏激,我不能一个人待着,我需要工作。
于是,我好好的改正了我的态度,把照片收进抽屉的最里面,坚持不让自己想他,一个月以后,生活与工作开始进入正轨。
此时已是年底,各方面的工作也紧张起来,社里经常加班,繁重的工作让人忘了时间,我整天埋头于大堆的文稿里,我自知工作卖力,可是年底评先进工作带头人时,我落榜了。
被评的自然是主编,还有其他奖励也没有我的份,我知道是前一段时间我态度恶劣造成的结果,我无怨无悔,就算我什么也没有也没关系,失去那么多了,还差什么呢?只要有工作我就满足。
我还是天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开会,出访,写稿,不知为什么,我写的稿子大部分都被主编退回。
他说我的字里行间缺失了一些理智言论,多了些个人色彩,且是悲观的个人色彩,时事评论版不适合这样的文章,我只好写散文给业余生活。
后来,版面编辑也有意无意地跟我说我的东西太悲伤,读者需要的是乐观,积极向上,看我能不能改改,我知道他的意思,好吧,我点点头,以后,我一个字都不会再写了。
我开始喝酒,以前的我滴酒不沾,现在,我可以成瓶成瓶地灌,却怎么样都不能让我减少心里的痛苦,弟弟离开了,也带走了我的一切,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我不能回到过去了?我没有答案,只有用酒精来麻醉,我突然之间,一无所有。
就在我又一次宿醉后,听到一个消息,主编死了。
他是在自家的浴缸里淹死的,死状恐怖,同样,警察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主编的妻子去外地出差,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雇了钟点工,警察盘查过,没有可疑之处。
后来,查出主编曾跟一个小服装店的女孩子有染,后来几度分手不成,二人反目,于是警察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女孩子身上,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把人放了。
主编的葬礼我去参加了,看着他两鬓花白的头发,想起与他共事了十多个年头,竟然不知道他也是个花心的人,他的才华一度是我的榜样,而现在,不再是了,当然我不能否认他还是个出色的领导。
他的妻子与儿女穿着丧服哭成泪人,我们一一与他们握手致意,然后我再一次看着天空中浮起的那些浓烟,又一度想起当初烧浔的情景,眼圈又红了。
经过选举,在三位主编候选人中我再次落选,而小我几岁的姚录成了主编,上任那天他在会上用谦虚的态度向大家保证一定做好主编工作。
是的,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做事谨慎,处事沉稳,选举他的人都是他的属下,能推举他,说明他是有实力的。
而我还是副主编,我不再求什么,这样一天天平静的过也不错。
下午下班后,我们按惯例去楼下的餐厅庆贺,要了一桌子酒菜,他挨个敬酒,气氛融洽。
吃过饭,大家提议去唱歌,我不会唱,可是又不能扫了大家的兴,何况是庆贺主编上任,我不能走,只好跟了他们去。
我有些醉了,独自去洗手间,之后,姚录跟两个同事起来,不知道隔档里有我,于是我听到他说,如果不是你们我还真当不了主编。
而另一个人说,当然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就算你不送我们人参,我们也会推荐你的嘛。说完他们爽朗的笑,我在他们走后才离开,人渣!我冷笑。
以后的工作平淡如水,我的审稿工作日渐减少,多半都由主编完成,用他的话说,我年纪大了,像那些小事不能麻烦我。
一时间,我成了社里最闲的人,我年纪大了?不过才三十岁,就年纪大了吗?如果我申请退休,也许他也会同意的。
是的,我没有吃人参,自然不会像他们那么精力旺盛。
我捧了报纸,喝茶,有时校一校稿子,下午来了个作者,说想要出书,来找我谈相关事宜。
我大概看了看他的作品,老实说,文笔不错,可是就差些情节与深刻的内容,在思想上有些浮浅,我一一指出,他也倒虚心接受了,表示再回去改改。
后来没半个月,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新书,很诧异。
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是主编同意出版的,并且有意无意地说我太苛刻,主编都说他的书很有新意,而且内容很有深度,会有广泛的读者群。
我问他,出书要了多少钱?他说出来的数字远远低于正式出书的数额,我就此事去找了主编,他说他认为这个作者很有潜力,说不定将来能一鸣惊人,而对于作品内容,他却含糊其词。
出书是要对读者和作者本人负责的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随便说出就出?
主编很不耐烦,说这是他跟大家商量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见跟大家说去。
然后端茶送客了,跟大家商量?这个大家显然不包括我在内,我不是属于他的“大家”范围,那些“大家”都吃了人参,意见自然跟他一样。
算了,不过一本书,也许我是错的,也许正好投大众读者口味也说不定。
我还是喝我的酒,父母不忍看我这样,张罗着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对于我而言,成不成家都一样,只要让父母开心,怎么安排都成。
说好晚上八点在咖啡厅见,可是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人还没到,我只好自己叫了一杯,边喝边听着音乐。
此时,身后有人说话,轻轻转过头,在暗淡的灯光下,我看到那个出书的作者正跟姚录坐在一起说话。
当然,作者跟编辑坐坐很正常,无非是谈谈稿子,市场行情等,可是,我却听到作者对姚录说的话。
姚主编,谢谢你帮我出书,这是上次答应你的另一半钱,能出书多亏你帮忙,要不是你,那个副主编绝不会帮我出的。
他?你要是指望他,那就完了,他懂什么?这都什么社会了?还死咬规矩不放,再说,你的书的确很有价值,不出太可惜了,要是他,一定会埋没了你这样的人才。
人才不人才的不敢说,只是他那样抨击我的作品实在有些过份,我又不好说,幸亏让我遇见姚大主编,您是伯乐,我不敢自称是千里马,可是有您的教导我也受益匪浅啊。
说完,两人得意地笑起来,我忍受不了这种相互拍马的情景,站起来付了帐就离开了。
第二天,老妈还为此训了我一顿,说人家去了不见人还等了那么长时间。
后来我们见面了,我对她没有什么感觉,她却同意跟我相处相处,渐渐的,我才发觉她是个很通情达理,又聪明伶俐的人,我也开始慢慢喜欢她了。
就在我们相处不足两个月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姚录出差时,在一个小旅馆里遭人杀害了。
身上的财物尽数被劫,据说包括他的手机,手表,现金,信用卡等一共有五万多。
据此调查后才发现姚录上任这半年多来一共贪污公款近十万元。
结果这笔钱被没收,他的妻子又哭又闹,警察还一一调查了与他有金钱来往的几个同事,也都被传到警察局去作调查,也包括那个作者,一失足成千古恨,书没出成,名声扫地,怕是他以后想出名不是靠书,而是靠这桩案子了。
姚录一死,大家只好重新选举,这次,他们选上了我。
生活总算有了起色,我用我一惯的作风,社里的气氛倒也平和。
在上任的第二个月,我们就决定结婚了,虽然快了些,但是既然两个人感情还不错,也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
结婚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条小路,走在这条路上,我牵着妻子的手,跟她讲着跟弟弟小时候的事。
她依着我,静静地听,此时已近黄昏,在小路上,天色也较黑些,那些婆裟的树影也开始变暗。
我望着远方,想着浔的相貌,心中再一次沉浸在那种伤感里,突然,我觉得手心里一空,紧接着,又有一只手插进来,小小的,软软的。
我猛地低下头,却看见七岁的浔正仰头看着我,露着他的小豁豁牙,可是我看不清他的眼神,似乎那里是两个黑色的洞。
哥哥。他叫,那叫什么树?他伸出手来指着前方。
我抬头看去,是那棵松树,那是松树。我说。
你说什么?我知道那是松树。
我猛地回头,身边站的是依然是妻,手心里握着的,也还是她绵软的手。
我叹口气,转回头,却陡然觉得一冽,因为我看见浔正站在树下向我招手。
我停住脚步,呆呆地望着他。
怎么了?妻摇我的肩,我回回头,她正张大眼睛望着我,说我怎么冒汗了?
我再看那棵树,更加暗淡的树影,没有浔的影子,是我眼花了吗?
我们回去吧,天晚了。我说。她点点头。
我们折回头往回走,可是分明听到背后传来浔的喊声,哥,别走,我迷路了,找不着家,我在来的路上等你,你怎么不管我了。
我猛然回身,路上,是他哭泣的背影,我向他跑过去,不,不是哥不管你,来,咱们回家。
我去拉他的手,可是回过身的却是二十岁的浔,哥,你来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我,可是,我回不去了,哥,你看,我身上全是洞,哥,救救我,你知道是谁杀了我的,对不对?
他对着我哭,我瞪着他胸前的一个个不断向外涌血的洞,他越哭越凶,泪像小河一样汹涌,一点点变成血色,脸开始融化,化去皮肤,化去骨肉,只剩一双白骨的手向我伸来,哥,带我回家。
那手猛地搭上我的肩,我不禁惨叫。
你怎么了?回过头,是妻,她脸色苍白地看着我,我怎么了?我大口地喘气,眼前空无一物。
你突然就跑开,然后盯着这片空白瞪大眼睛直冒冷汗,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我甩甩头,紧紧握着她的手,什么也没说,我不想吓坏了她,我们回家吧。
躺在床上,我碾转反侧无法入睡,又想起刚才的事,是我的幻觉吗?却又为何如此真实?
是的,浔是冤枉的,到现在我都没有给他找出凶手,他怎么能冥目?
浔,是哥的错,是哥对不起你,我想着他竟然哭了,为了不惊醒妻,我去洗手间,反锁了门,这才咬着毛巾痛哭。
哥。有人喊我,我停止哭泣,抬起头来,看见浔的脸出现在镜子里。
浔!我呆望着他。
哥,别难过,我知道你心疼我,只是,放心吧,哥,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我哪儿也不去了,不出国了,让爸妈把那笔钱给你吧,我用不着了。
哥,我早就应该这么做的,是我太自私,不懂事,明明知道你那时候需要钱结婚,可是我却要出国学习,你是为了我才跟茵分手的。
哥,是我对不起你,这个嫂子很好,你能结婚我就放心了。
浔,告诉我,是谁杀了你,哥给你报仇。
我扑在镜子前,企图抚他的面颊,可是指尖却只是触到冷冷的玻璃。
他垂下头笑了笑,哥,这都过去了,不重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死,活着,只会拖累你,你做的对,哥,做的对。
说完,他在我面前开始消失,眼前的镜子里还是我,面容憔悴的我。
外面有人在敲门,是妻,我开了门,她担心地看着我,问我在干什么?问我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像哭过一样,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搂着她。
度完蜜月,心情好了很多,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累是累,可是很久没有四处旅行的我,这一趟下来,终于能让一路美景将心事赶走也不枉是一件好事。
我们买了很多礼物送给亲戚朋友同事,上班后,他们都说我变了,人变得开朗了,看来还是结婚好啊。
回到办公室,坐在主编的位置上,我有种满足感,虽然责任又重了些,可是我熬到现在能爬上这个位置也实在不容易。
秘书给我端上一杯清茶,我告诉他这样的事以后我一个人做就好了,他只是我工作上的助手,不是我的仆人。
他很高兴,只是忧郁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吧。我放下稿子。
我听他们说,这个位置很邪门,你看,前两任主编都死于非命,您可要小心。
我微微一笑说,行得正,站得直,我不偷不贪怕什么?他说是是,然后出去了。
我望着眼前这张办公桌,心里坦然。
办公室在十六楼,上班下班要坐电梯,我每天都提前十分钟到,推迟十分钟走,一是避免电梯高峰,二是也让别人知道我的工作态度。
周四,我因为一篇稿子到快九点才审完,出了办公室才发现大家都走光了。
刚要离开,却发现走廊尽头的打印室还亮着灯光,难道是小刘还在加班?
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没人应声,可是我分明听见里面复印机的嗡嗡声。
我推开门,果然,复印机的灯亮着,并且在一遍遍地不知在复印什么,难道小刘又忘了上次的教训在这里私自复印自己的东西?
我皱了皱眉,这个小刘什么都好,就是爱贪小便宜,常常拿自己的东西来这里利用下班的时间复印。
我走过去,拿起复印好的东西,突然觉得背后一凉。
这是张图片,是第一任主编死在浴缸里的照片!
他瞪着眼睛整个身体都泡在水里,我慌忙将它丢下,小刘为什么要复印这个?
我伸手去关复印机,可是怎么关,它都一遍遍无休止地工作着,那一张张的图片就从里面飘出来,主编那双眼睛似乎充满了整个房间!
盯着我,死死地盯着我,我向后退去,准备离开,背后却撞上什么,转过身,却看见姚录咧着嘴看着我笑。
嘻嘻嘻,这是他固有的笑声,是那种发现了什么好笑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那种嘲笑,却又不敢让人听到般的虚伪。
他咧着嘴,是的,因为他的嘴不可能闭合,因为从左耳到右耳,连同嘴形成一个大口子,他的舌头搭在一边,歪着头,脖子里正往外冒着污血,地上已经成了一片血洼。
你已经死了,回来干吗?
他只是嘻嘻嘻嘻地笑,不回答,不说话。
身后,复印机里还是在“哗哗”地向外如水般涌着一张张可怖的图片,然后,从桌子下面涌出大量的水来。
一双手,被泡得发白的一双手,正一点一点,从桌下伸出来,企图捉住我的脚。
我不顾一切地举起椅子冲过去砸向姚录,然后趁机夺门而逃,还好,电梯正等在那里。
我冲进去,电梯适时地关上门。
我靠着电梯,气喘如牛,也许是我的错觉吧,可能是出去一趟没有休息好,明天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回到家,妻不在,桌上留了字条,说是同学聚会,冰箱里留了饭。
我洗了个澡,用微波炉热了饭,边看电视边吃,然后洗了碗,去书房看书。
翻了半天,才想起那本看了一半的书放在卧室了,其实那书我看过不下十遍,因为情节感人,所以总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拿来翻翻。
妻也爱看,常常跟我抢,我让着她,总等她看够了才拿回来。
妻喜欢在躺在床上看,劝了她多少次会伤眼睛,可是她就是不听。
我翻起她的枕头,果然看到了那蓝色的书皮,就在我拿起书的时候,也带下来一封信。
很奇怪,我们的信现在都用电子信箱,很少看见她用笔写信或是收到纸质信函。
只有信纸,没有信封。
我将纸展开,很明显是男人的字体,铿锵有力,而信的内容却温宛多情,严然是一封情书,落款没有名字,只画着一艘船,时间是上个星期。
妻是个医生,工作认真负责,医术高明,家里的奖状多半都是她的,她为人和气,受到病人的欢迎很正常,她的电子信箱也常常爆满,其中不乏一些仰慕的信件,但她多半都一笑置之,然后统统删掉。
可是这封信她却好好的收在她的枕下,又是何解呢。
我将书跟信好好放回原处,回到书房,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只好站在阳台上抽烟。
大约十点半左右,我看见楼下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大概是奥迪,车正好停在我家楼下,然后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女的手里还握着一捧鲜花,在路灯下格外刺眼的鲜红,那是玫瑰,那鲜艳的红色映衬着妻的脸也是格外迷人。
而那个高她一头的男人穿着黑色的夹克,应该是那种被女人们称之为帅气的一类吧,此时,他正轻轻搂着妻的肩,妻只是微微躲了躲,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我不想加上我的想象力,这应该是妻的同学,也曾是她救助过的病人,送花只是为了感谢,送她只是为了安全,亲了她的颊只是为了礼仪。
然后车开走了,妻站在原地一直等车消失踪影,才转身上来。
走廊上,我听到她低声轻唱。
随着她的高跟鞋,到了门外,她才停止歌声,然后开了门看见坐在电视机前的我。
吃了吗?很平常的口气,我瞟了一眼她手里的花说吃了,你呢,上哪玩去了?
跟一大群同学上半山餐厅唱歌,你看,他们还拿我当小姑娘呢,知道吗?班里每个男生都送女生花了,说今天是情人节,呵呵,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玩这个。
她容光焕发地将花插进花瓶,随手扔掉了我送她的天堂鸟。
我转过头继续看电视,她哼着歌进了洗手间。
因为下班遇上的事跟在阳台上看到的情景让我很久才入睡。
当我听到那一声尖叫时,我猛地张开眼睛,天已经大亮,我光脚冲出去时,看见妻瞪大了眼睛望着花瓶。
我这才注意到,那些娇嫩的玫瑰被从中央齐齐剪断了,残花散了一地,一桌,像极了一滩滩的血。
怎么会这样?我也觉得有些悚然,突然就想起了昨天下班时的事。
不可能吧,我冲过去将花枝丢进垃圾桶,用扫帚将花瓣清扫干净,然后丢进了垃圾道里。
回来,妻依然脸色发白,我揽着她的肩,她有些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天哪。
不怕,不怕。我劝她,可是这样无法解释的事情我拿什么来当借口?
妻坚持要去上班,提前一步离开了。
我去洗手间刮胡子,就在转瞬间,突然听见背后的浴缸里传来水声,我转过身。
是的,水声很急,我有些四肢冰冷,心里祈求千万别看见什么。
我闭了闭眼睛,走上前去一把拉开帘子,水声骤停,浴缸里干干净净的,水龙头也关得很紧,一滴水都没有。
就在我要放下帘子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我回过头,看见一滴鲜红的血出现在浴缸的最中央,接着又是一滴,那鲜艳的血液落在洁白的浴缸里,格外渗人。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竟然看见姚录的头正从天花板上伸出来,头朝下,眼睛瞪着我,血从他的嘴里一滴一滴地落下,然后,就是他的笑声。
水,从浴缸的下水孔里冒上来,像烧开了一般沸腾着。
我站在原地发着呆,不知道害怕,不知道离开,看着浴缸的水不断上升,变满,溢出,接着,有一只手握住了我的。
我低下头,是后脑陷进去一块的浔,浑身是血地看着我……
“叮铃铃——”一声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炸响,让我这才突然回醒,失声尖叫,然而,四周的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没有水,没有血,更没有浔,而电话还在外面响。
我冲出去接电话,那边是一连串的咳嗽声,似乎嘴里还含着一口水,含糊不清。
水!我猛地打着冷颤,谁!我吼。
我,是我,没什么事,就想听听你的声音。是妻。
我顿时松口气。
你怎么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你今天休息,去菜市场买条鱼,晚上我回家给你烧鱼吃吧,最近看你脸色不好。
哦,没事,我,好的,我去买。
好的,我要去忙了,你按时吃饭。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可是我保证,我的确听到了那咳嗽声是个男人。
我不能待在家里,我需要站在阳光下,去买鱼。
星期六一大早,市场上已经人头攒动了,在人群里,我的心才能略微平静。
卖鱼的大婶给我挑了条中等的在杀,我去口袋里拿钱包,却摸到厚厚一包东西,拿出来,展开,不禁失手,是照片!
缸里那双眼睛,它是什么时候跑进我口袋里去的?
你的鱼!卖鱼的大婶不耐烦地甩甩手里的黑色塑料袋,我这才掏出钱包来付了帐。
转身匆匆地走,远远的才敢回头,可是刚才落了那照片的大水盆里除了翻动的水花什么也没有,也许是那个大婶扔掉了吧。
这样想着我转身准备再买些青菜,可是却觉得手里的袋子越来越重,我停下脚步低头看看,手里的袋子变大了,还不断往下滴着血水,我慢慢打开袋子来,却徒手将它丢远。
行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被一条乱动的鱼吓得面无血色,明明,看见的是姚录那咧着嘴的脑袋在黑色袋子里冲我笑。
错觉,一定是,不然光天化日怎么会有鬼怪出来生事?
我蹲下去捡起那条溜滑的鱼,然后买了些青菜,这才回了家。
站在门外,犹豫了很久才进去。
鱼洗好放在盆里,它没有再变成人头,我回到床上去准备睡一觉,迷迷糊糊地,听到厨房有动静,是切菜的声音,原来是妻回来了。
头昏昏沉沉的,又继续睡了一会儿,这才清醒了,看看表,已经下午四点了,睡了两个小时。
坐起来,听到厨房里是妻的切菜声,切菜?不对,刚才听到切菜时我扫了一眼表,是两点二十,现在已经四点了,她有多少菜要切?
可是,从厨房里清清楚楚地传来她切菜的声音,咔嚓,咔嚓。
我下了床向厨房走去,在厨房门口,我看见她的影子投在地上,我这才松了口气,是她。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说着就进了厨房。
可是却愣在原地,站在案板前的人还在一下,一下地切,切的不是菜,是那条鱼,已经被跺得血肉模糊,而跺它的人不是妻,是我!
他扭着脸看着我,一脸邪邪地笑,手里握着尖刀,不断地跺着。
我慢慢向后退,转过身,看见主编浑身湿淋淋地站在墙角地上一片水浸,然后又是嘻嘻的笑声。
姚录站在洗手间的门缝里向我看过来,然后,我又看见浔,蹲在阳台上,侧着脸看着我,血从他身上叭嗒叭嗒地往下掉。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总缠着我!走开!我冲他们大吼大叫,然后就醒了。
张开眼睛,自己还在卧室里,四下一片宁静,头疼得厉害。
我侧耳听听,厨房没有任何声音,我抬手擦了擦头上的汗。
快七点,妻打电话来说不能回来了,有个病人要急救。
我只好给自己煮了碗方便面吃。
那条鱼被我丢进冰箱最深处。
吃过饭,我下楼去散步,我觉得自己正在向神经崩溃的边缘前进,妻是医生,也许她能帮我,可是我又怎么跟她说这些?在她看来一定是认为我神经出了问题,唉。
我沿着马路没有目标的前进,路边是酒吧,我急切地想进去喝个酩酊大醉。
一仰头,一杯酒就下了肚,感觉真不错,于是一杯接一杯,很快喝光了一瓶,却没有醉的意思,想再要一瓶,一扭头,仿若错觉地看见妻从身旁经过。
我甩甩头,扭头,看见她正搀着一个男人的胳膊笑盈盈地向外走,那个人就是送她回家的那人。
我付了钱追出去,正好看见他们上了那辆黑色的奥迪,然后扬长而去。
酒,不一定能捂着你的眼睛,让你什么都看不见,愁是火,用酒只能越浇越烈。
回到家,妻已经睡了,探起身看看我,皱皱眉头,扶我进洗手间。
我没醉,却装得摇摇晃晃,病人怎么样了?我问。
不错,脱离危险了。她说。
是吗?那什么今天有一个叫桑舟的打电话说你没上班?
不可能!我今天明明跟他……我是说,我是说,她吞吞吐吐,我装作睡着,什么也不想听。
能开奥迪车的人不多,能在一个小医院拥有这样车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院长的儿子,小妻两岁的桑舟。
真正睡着后,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下了班回到家,竟然看见桑舟穿着我的睡衣,用我的刮胡刀在刮胡子,妻正在削苹果,等他出来,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给他吃。
而对于我,他们根本不加理会,妻竟然还让我下楼买菜,要做给桑舟吃,我的怒火喷发,冲上去拿起水果刀一下划破了妻的胳膊。
我听到她惨烈的哀叫,叫声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她返身夺我的刀时指甲陷进我的肉里那种痛都是那么真实。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你红杏出墙,你背叛我。
我用尽力气,就在刀尖快要刺中她头部的时候,我醒了,其实是疼醒了,我渐渐地看到我面前一脸惊恐的妻。
你怎么了?我问。
她喘着气不能回答我,然后,然后,我看见她的眼神向上移,我看见了那把刀,握在我手里的那把刀,还有腕上被她的指甲划出来的血印。
而她的胳膊上,一道伤口正在泊泊地往外冒着血,我猛地丢了刀,她跳下床蜷在墙角。
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明白了。
现在,我坐在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妻胳膊上缠着纱布站在窗外看着我,然后转身离开。
我想起了那个梦,所有的梦,第一个梦,梦里,浔板着脸在父母面前要那笔钱要出国,而我跟未婚妻则站在一边,母亲看看我,看看他。
他头头是道地说着自己的理想,说我们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的学业,要误了他的前途,如此偏心哥哥。
于是,母亲点了头,未婚妻转身离开,我看见浔那张得意万分的脸。
接着,他接过母亲递给他的存折快步跑开,我追着他,梦里一直追着他,看着他进了银行,看着他数着几万块钱,再看着他揽着未婚妻的肩回了自己的住处。
我踢开了门,手里不知怎么多了块砖,未婚妻不见,只有他,站在屋里数钱。
于是,我用力砸向他的头,桌上,有他的水果刀,我一刀又一刀地刺进倒在床上的他的胸膛,于是,梦醒了。
第二天,传来他被杀的消息。
第二个梦,我在主编的家跟他讨论我的稿子的事,他围着我一遍遍地责骂我,将我的稿子撕得粉碎并扔在我的脸上,说我不负责任,对工作敷衍了事。
还说如果不是因为跟我共事已久早就把一脚踢开了,那么多伤人自尊的话让我受不了,我把他推倒了,他撞在门上晕了过去。
于是,我把他拖进浴缸,加满了水,看着水没过他的身体,我紧紧压着他的肩,他瞪着眼睛盯着我,直到不再挣扎。
第三个梦,姚录在我面前摇晃着一大把的钱,他那副得意的,卖弄的嘲笑的脸在我面前转来转去。
跟主编一样,用尽字眼来羞辱我,于是,我也把他打晕绑起来,可是他却醒了,笑话我还敢这么干,等他将来报了警一定会让我不得善终,然后就是那种笑声。
我受不了他的这副德行,便将他的嘴活生生地撕开,然后把他杀了,还拿走了他的钱。
我在梦里时,意识很清醒,感觉很真实,可是,却告诉自己这只是梦,是梦,梦醒来,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
所以,在梦里,我可以发泄,可以痛快地杀死他们,谁又知道,我的梦,却是他们的终点。
我看着手上的伤,除了妻抓破的以外,还有一道划伤,那是我在梦里用剪刀剪那些玫瑰时弄的。
妻在走前说,那天早上醒来,看见我手里的剪刀,然后看见一地的断花,而我,却是一副无辜的神态就知道。
我有梦游的毛病,可是,我却又是怎样在睡梦中跑去百里之外杀了姚录,却无法解释,也许,现在的我也是在梦里,一个很长的噩梦,等我醒来,浔还是在一旁看着书,办公室里,主编还是半开玩笑地端着茶杯拍拍我的肩,而姚录也还是用他固有的笑声来对每一个人,杀人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今晚,我又做梦了,梦见浔站在我们散步的小路上向我招手,哥,我在原路等你,你带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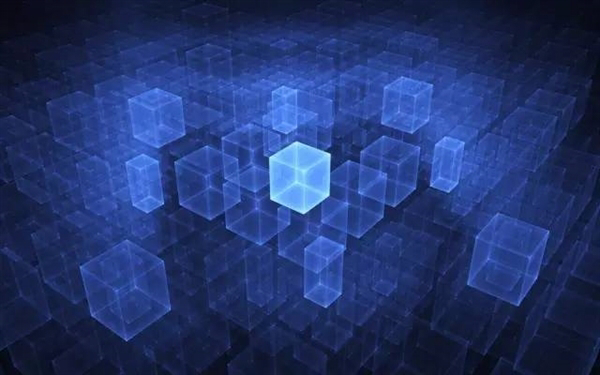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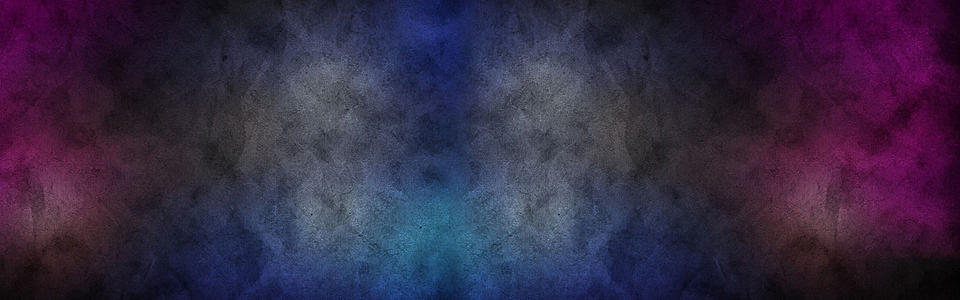




吓人
谢谢捧场
真的赞!
谢谢捧场
写的不错
谢谢
终于明白了;其实凶手就是自己
对,聪明!
这是小说吧….
毫不隐瞒的说,这是小说
这个小说让人看完觉得故事片大宝挺好的,尤其十分可惜的是小编主人公的那位弟弟意外英年早逝,所以愿世间少无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愿笔者才华横溢以及你弟弟那样的好孩子们都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谢谢你,也祝愿你一切平安幸福。
成才之后 娶了你老 母 ✗笑哭了✗
哎哎,大家友善回复啊,不要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