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儿五岁就被父亲卖进了戏班子。
从此结束了她的童年,走上了艰辛坎坷的人生之路。
学戏、练基本功不是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吃不饱饭,还要给师傅、师兄、师姐们浆洗衣服,小小年纪的她就已经吃尽了苦头。
但是有了委屈却是不敢哭的,因为师傅的那根鞭子着实让她害怕,身上长长短短、新新旧旧的伤重重叠叠,睡觉都不敢躺着,实在忍不住,就趁着打水的工夫在河边哭一阵,也是不敢出声,怕被人听了告诉师傅去。
回来,被人见了也只能说是风吹了沙在眼里。
那是她最最黑暗的日子,每每想起鼻子都要发酸,直到现在她还是很怕师傅,尽管师傅总说是为了她好。
日子一天天过着,十年后,戏儿长成了大姑娘,戏不但唱得好,台上的功夫也自然了得,那可是师傅打断了多少根鞭子才练出来的啊。
戏班子的人不多,两个花旦,三个武生,两个老生,还有三个吹鼓手,加上师傅十来个人,走南闯北,到一个地方就搭台唱戏,有些地方富的就能赚些钱,穷的地方也就赚几个窝头,有时甚至连个窝头都赚不到,可是师傅却好象并不介意,反而还很高兴,钱却也不缺。
戏儿一直都是想不明白,也不敢问,师傅让去哪就跟了骡车走,让唱就唱,问多了又要挨鞭子了。
那是个九月天气,他们的戏班子一路向座深山走去,戏儿此时已经是班子里的台柱子,刚刚在个大村唱了几天,本来她会以为可以休息休息,可是昨天下午师傅却告诉他们,今天要去另一个村子,戏儿想去赶赶集的计划破灭了,一大早,他们就出发了。
戏儿现在坐在骡子车里被车颠簸着开始打盹,不知几时,再掀帘远望,已经走进绵绵群山之中了。
虽已过午,但在这群山之中,毕竟没有那么明朗,阳光被大山隔着,山沟里只是片片暗紫的雾气,阵阵山风吹来只觉阴冷。
车在村口停下,众人下了车,一个槐梧的大汉带着几个人迎上来,戏儿远远地看见远处错落的十几户人家,在这样的地方能有几个人来听戏?戏儿这样想着,大家便已经动手开始卸车了,而师傅跟着那人进了一方院落。
这是个不大的四合院,尽管红柱绿瓦,但年久失修,已然破落,三面厢房就更加破不堪言,整个院子里杂草丛生,墙上生着霉斑,发黄的窗户纸破了大洞,一片片地挂在窗棂上,还有蜘蛛将网织在发黑的墙角,几只黑鼠匆忙地从一道墙冲到另一道墙角去。
戏儿皱着眉毛看着这一切,这以前也必是个富人家的宅子呢。
领路人是村长的儿子,叫马择,他与师傅客套一番后便与来人一齐帮着大家动手打扫院子。
就这样,戏班子便在这个不大的小山村安顿下来。
正像戏儿想的,村里人并不多,数来数去也不过十来个人,而且多数都是老人,像马择这般年纪的也只有一两个,据说是他们早已去了外面闯世界了,而马择也打算明年离开。
话说待大家都休息安排后,戏班子便在傍晚时分搭台开锣了。
村里人是许久没有听过戏,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过戏,见这戏班子一来都无比兴奋,扶老携幼地前来看戏,看懂看不懂且先不讲,单是这一身身的装扮,一张张红妆,一阵阵热闹的锣鼓喧天也足已吸引着他们。
还是戏儿唱主角,唱的是贵妃醉酒,台下鸦雀无声,只是仰着一张张无知而痴迷的脸望着台上,戏儿嘹亮的唱腔在山间回荡着悠扬曲调。
一出唱完又一出,直到夜深沉,大家才打着哈欠各自回家去。
戏儿一身疲惫地卸妆换衣,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师傅今晚要安排她唱三出戏,而奇怪的是整晚竟然都不见他和另外两个师兄。
收拾停当,吃过晚饭,还是不见师傅、师兄,只好回屋睡觉。
师姐莫梅起初直抱怨房子破旧,还有老鼠不断的磕墙让人没法睡,念叨几句便睡去了。戏儿唱得累了,可是就是睡不着,过了好久,觉得口渴便下床去倒水,却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又被轻轻磕上,接着就是三个人影悄悄地向着正屋去了。
黑暗中,戏儿看出那是师傅和师兄白威、郑龙,他们怎么现在才回来?而且郑师兄还拎着一口箱子,那是什么?戏儿在门缝看着他们进了屋,随之点亮了蜡烛。
戏儿回头看看莫梅,她正沉睡着,于是她轻轻打开门走了出去,其他屋也都传出了打鼾声。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窗上已经挂了帘,她只能在一个缝隙中往里看。
师傅和两个师兄手里各拿着一个蓝瓷花瓶在看,表情无比激动,而在炕上还有一些首饰。
只听师傅说:“我说得没有错吧,那个财主的墓里不会少了宝贝的。”
“师傅,您怎么知道这个村有个财主的?”说话的是大师兄。
“我以前就在这个村做过活计,所以知道,前段日子我打听出这个财主死了,而守坟的人也只有一个孙子,用不着怕他什么,这些东西随便卖卖也能值几个钱的。”师傅压低的声音里隐藏不住的兴奋。
“师傅,万一他那个孙子找了来怎么办?”另一个师兄怯怯地问。
师傅看他一眼,说:“他整晚都在看戏,怎么会知道?而且咱们天亮前就走,等他们发现了也迟了。”说完不禁嘿嘿暗笑起来。
原来,师傅他们明着是唱戏,背后却是在干盗墓的勾当,这么多年我竟然都不知道!难怪师傅总带大伙到这穷地方去,反而总有花不完的钱,这其中原因就是他们不断地在盗取墓中的宝贝,而自己无形中不也成了他们的掩护吗?戏儿想着害怕起来,盗墓可不是小事,被人发现可不得了。
该怎么办?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离开他们吗?离开了自己该去哪儿?如果不离开,那么自己就要一直做他们的同伙吗?不,这万万不能。
一个个矛盾的问题在她脑中徘徊着,这时,她突然看见了墙角一丛开着小蓝花的草,于是有了主意。
“师傅您回来了吗?”戏儿在外面敲门,于是听到里面一片压低了声音的慌乱,只听师傅问了句:“谁啊?”却总不见来开门。
“师傅,是我,戏儿,来给您送饭的。”
“不必了,我已经睡了。”
“师傅,您晚饭还没吃,睡着不舒服。”戏儿说。
闷了好一会儿,师傅才没有好气地开了门。
“放桌上,回去睡吧,天亮前还要赶路。”戏儿点点头出去了,却不见了满炕的宝贝。
她径直回了屋,关好门后看见师傅这才掩门。
夜更重了,戏儿躺在炕上,身旁的师姐梦呓着翻了个身,她又一次下了炕轻轻推门出去,站在外面四下看了看,院子里除了人的鼾声就是虫声,而师傅的屋里却还亮着灯,她眉头一皱想,难道我弄错了?那株小草不是安心草?
她再一次摸到窗下,听到的是深沉的鼾声这才放下心来,于是她伸手试探着推开了门,师傅师兄三人并没有什么动静。
她走到他们身边推推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才向着炕边的一个黑箱子走去,她看见他们将宝贝藏在这里面。
月光黯淡地照着山路,戏儿吃力地向山上走,汗水顺着额头流进衣领,她却顾不上擦,直到拐进一个山坳,她发现了一个小黑洞,这才停下,喘口气,将黑箱子推进了洞口,又用草盖好,并一路消了脚印。
她抬头看看天,然后匆匆返回,院子里依然一片宁静,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她回到屋里躺下,半夜只是起了阵风。
她是被师姐推醒的,张开眼睛,天已大亮,她揉揉眼睛坐起来。
外面天气很好,空气里有股清新的味道,大家都站在院子里锻炼,却不见习惯早起的师傅,于是有人去敲师傅的门。
好半天,才传来师傅的怒喝:“谁啊?有事吗?”
外面人道:“班主,该起了。”
又半晌,忽听师傅惊声问道:“几时了?”
“怕是已到卯时了。”
“什么!!”师傅似乎是小跑着冲出来的,他先看看外面天色,再看看满院子的人,两个师兄也追了出来,显然也是一脸惊讶。
“班主,怎的了?”外面的人问。
师傅看看他再看看大家,似乎有些懊恼,于是摆摆手,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上路。”
说完回身进了屋,立时又冲出来大声问:“谁进我屋了?”
所有的人都摇摇头,白、郑二人望着他,然后突然醒悟般抽身回屋,紧接着出来,脸色也是张慌的。
师傅再次回去,白、郑二人也跟着,大家听到屋里传来翻东西的声音,此时,门外突然有人吵吵嚷嚷地冲进来,师傅扭头看去,是四五个中年人,手里拎着木锨和镰刀,一个个目露凶光,凶神恶煞地瞪着院子里的每一个人。
“叫你们管事儿的出来!”带头的一个黑大汉叫着,他身后跟着马择。
“有事么?”师傅不一会儿从屋里走出去,望着他们心下猜出几分他们的来意,却不露声色。
“你就是管事儿的吧,废话少说,快把东西交出来,咱们没事,不然,你们休想活着离开!”除了知情的人,其他人都面面相觑。
师傅却还是镇定自若:“这位兄弟,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们是穷唱戏的,只想挣几个小钱度命,你们总不会连我们这些讨饭的家当也要吧?”师傅面不改色地说。
“我们虽然穷,也不至于去抢,就你们这些破烂东西我们还看不上,我劝你别给自己找麻烦,你们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
“说实话,我们还真不知道。”师傅瞪着他说。
“那我就告诉你们,昨天夜里我家的祖坟让人刨了,里面的东西全被盗了,我们住在这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你们昨天一来,坟就被刨了,不是你们,还能是谁?”
“嘿,这位兄弟,我们也穷,也缺钱花,但也不至于干那缺德事吧?你们如此兴事问罪可有些莫名其妙,我们也算是在江湖上走动的,这名声要是传出去,你叫我们以后怎么混饭吃?再说,谁又知道你家祖坟的事?”师傅倒也不依不饶起来。
“你别强词夺理!”
“你们说我们盗了墓,那么,证据呢?谁看见了?”院里有人也叫嚣起来。
“证据现在就在你们这院子里!现在我们要搜!”
“搜?好,如果搜出来我们把命放在这儿任凭处置,如果没有,你们得还我们一个公道。”师傅双手在胸前一抱。
来人没有开口四下散去搜东西,半晌,又都聚起来双手空空。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把东西藏起来了?”另一个中年人说。
师傅沉下脸来:“搜也搜了,东西没搜到就要冤枉人,你们是认定了我们做了贼,那我们在你们的地盘上,白的也是黑的了,你们想怎么说都行,反正光天化日,栽赃陷害也不是没有,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村里有人早就掂记着,现在趁此机会陷害我们。”
听了师傅的话,领头人与其他人对视着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好一会儿,村长说:“好,就算你们是清白的,不过,找到东西前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口气坚硬不容分辩,说完带头离开了,门外留下几个人守着。
人一走,师傅倒吐了口气,然后环视院子里的人,其他人都慌忙地摇头,“我们绝不会干此事的。”
师傅的目光最后落在戏儿的身上,“你昨晚在哪儿过的夜?”不等戏儿回答,师姐先说了:“她昨晚跟我在一屋。”师傅这才点点头,然后示意和他一屋的两个师兄回到屋里,让其他人待在自己的屋里不许出来。
“你们说,那东西能去哪儿?”表面是问,话里却含着怀疑。“师傅,我们昨晚一屋,早上一起醒的,昨晚睡那么死,怎么会知道?”白威抢先辩白着。
“是啊,师傅,平时睡得没那么死,我们也是很纳闷,师傅,难道,真的有,鬼?”一个“鬼”子说出口,三个人都有些惊慌。
最后还是师傅比较镇静:“不可能,又不是头一回,都平安无事,哪有鬼?有鬼也是人在做鬼。”说完,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大叫:“戏儿,过来。”
戏儿听这一叫,心里着慌起来,难道他们怀疑了?她慢慢地站起来向着师傅走去。
其他人都探着脑袋看,纷纷猜测着这事是不是与戏儿有关。
“什么事啊,师傅?”戏儿轻声问。
师傅关了门,戏儿被三人围在屋里。
“戏儿,你在戏班子里也有十年了,从来不说慌,现在告诉师傅,你明白刚才那些人说的事吗?”戏儿抬头看着他们,也许他们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知道真相,只是在试探她,又不能明说。
于是戏儿摇摇头。
“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要是知道就说出来,师傅不怪你,不然的话……”
“师傅,戏儿从不骗人,真的不知道。”戏儿坦率地望着他们。
“你要是知道什么一定告诉我,不然让我知道你知情,小命难保!先回去吧。”师傅又问了其他人同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对于宝贝的失踪查出个蛛丝马迹来,可是却毫无线索。
第二天傍晚,那伙人又来了,这次没有带什么“凶器”,而是一脸笑意地来,还带来了一些礼物,一进门就赔情道歉起来:“当家的,上次是我们太失礼,错怪了你们,这次特来向你们道歉赔罪,希望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说着递上了些不算厚重的礼品,被师傅伸手挡开:“这位兄弟,话说清楚再收不迟。”
村长笑道:“上次是一场误会,我们承认是冤枉了你们,万望恕罪才是。”
“东西找到了?”师傅问。
“嗯,应该不是找到了,而是它们自己回来了。”一句话倒让其他人有莫名其妙,尤其是戏儿。
“那天我们走了之后,派人偷偷守在坟墓边,说句不恭敬的话,我们是想,也许你们之中偷了东西的人害怕,会再将东西放回去,其他人就四处找,可是今天中午换人看守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那些东西又回来了,事情虽然很奇怪,但足以证明我们冤枉了你们,我代表全村人向你们表示歉意,晚上到我家,我请大家喝酒,表示赔罪。”
“嗨,既然是一场误会,说清楚就成,什么赔不赔罪的。算了。”师傅大度地一扬手,大家便和颜悦色了,约好晚饭时,全都聚到村长家吃酒。
戏儿听了村长的一席话,很是不解,自己明明把东西放在那个黑洞里了,为什么会又自己回去了?太不可思议了,莫非是那村长故意设了圈套骗人的?晚上的摆的是鸿门宴?只是为了给村民一个交待吗?不行,好事不能办成坏事,如果不是自己不知道那个坟墓在什么地方,一定不会半路将它们丢掉的。
月亮已经升起来,戏班子上上下下开到村长家中,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盘子,虽然多半还是上不了席的菜,酒也算不上好酒,但盛情难却之下,大家也是畅怀痛饮,席间,戏儿称自己肚子痛,趁机溜了了出来。
月色比前一天晚上亮了些,戏儿又走了前一天晚上走过的路,没有了负担走得轻快了许多,转眼,就看见了那个山坳,她快步赶上去很容易找到了那个黑洞,她伏下身将手伸进洞里,一下子就摸到了那个黑箱子,她将箱子打开,月光下,各种瓷器和几样不算太值钱的首饰发着美丽的亮光呈现在戏儿的眼睛里。
果然,他们设下了骗局,当戏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迟了,因为她发现她的身后站了三个人,都是村里的人,在他们的目光里戏儿只觉得双腿发软,绝望油然而生。
三人不由分说绑着她连同那箱东西统统带回了黑大汉家,师傅及众人正在欢饮,戏儿就被人用力地推进了门倒在地上,大家不由惊愕之极。
“管事的,看来,今天这顿饭吃得很值得啊。”村长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师傅恶狠狠地站起来走到戏儿面前,在他心里,戏儿是个骗子,是个小偷,是个竟然敢黑吃黑的黑心贼!不禁怒从心中起!
“戏儿,我养了你十年,没有亲情也总有恩情,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他这一语双关的话让戏儿无从申辩,一肚子的话她说不出来,就是说了,师傅又怎么会相信她?
师傅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但心里的狠怎么能一记耳光了得?
“兄弟,是我错了,是我收错了徒弟,现在人赃并获,人就交给你们,随你们处置吧。”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我们村里有规矩,凡偷盗者,一律按偷盗物品贵重责罚,或断指,或断臂,现在是盗墓,惊了死去的祖先,就该活埋向祖先赔罪!”一句话落惊得戏儿一身冷汗,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她抬着苍白的脸望着一屋子的人。
这时,莫梅说话了:“戏儿会盗墓,打死我也不信,她平时很听话,而且你们看她手无负荆之力,怎么会盗得了墓?”
“说得也是,凭她一个小女孩儿,我看她连刨坟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认为她一定有同伙!”村长说着又盯上了师傅。
“戏儿,你老实说,是谁帮你盗墓的?”师傅的眼神凶恶地瞪着戏儿。
“师傅,我。”戏儿泪流满面,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不说?好,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你这个不争气的丫头,不但丢了我的脸,还连累了大家。”说着就对戏儿拳脚相加地打起来,戏儿尖叫着在地上打滚,旁人来劝,师傅大叫着:“我就是要打死她,看那个帮她的人出来认罪不。”说完,继续狠打,此话一出,又怎么有人敢再出面?只任师傅一脚脚的踢打着,他如今不止是要出心头之气,还要灭口,不然他怎么收场?
于是他顺手拿了墙边的斧子,朝着戏儿的头就一斧子背儿,戏儿立时没声儿了。
村长见此这才惊慌起来,他只是想借此惩罚这些外地人,可是如今却到了弄出人命的地步,他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众人也呆在原地,片刻才想到上前劝阻,但是戏儿已经只有进的气没了出的气,脸色死白,瞪着大眼睛,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血从鼻子和嘴里往外涌,样子极为可怜。
“管事的,你怎么下手这么狠?一个小姑娘怎么能经你这么打?”村长吼,师傅忙丢了斧子痛哭起来:“哎呀我的戏儿,师傅不是有心的,师傅只是生气,怪你不争气,师傅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戏儿,我的孩子。”
其他人见状也知道戏儿必是活不成了,都不由哭起来。
莫梅哭着扶起戏儿,教她坐起来,她这才吐出口气,咬着牙说话,却只说了三个字:“我,冤,枉。”说完头一歪,张着眼睛死了。
白师兄将戏儿抱回宅子里,将她放在炕上,莫梅给她洗脸,换衣服,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像样的,每件衣服都打了补丁,甚至一碰就要破了似的单薄。
村长和一些村民来了,说了些安慰的话,毕竟东西失而复得,人家也陪上了一条命,也不再追究了。
等人全走了,莫梅看见炕上多了件红衣服,红色的,矮的立领,前胸绣着大红的牡丹,宽袖,衣服下摆缀着红色的流苏,每个流苏上还串着红色的小珠子,这衣服是漂亮,而且还像是新的,鲜艳的颜色依然华丽炫目。
于是她将衣服穿在了戏儿身上,大了些,但是如果戏儿活着,一定会喜欢,想必是哪个村民可怜戏儿才送了这衣服来,戏儿,醒来看看,这衣服多好看,莫梅想着哭了。
村里有讲究,孩子死了不入葬,因此,众人便将她放在一个山谷里,随便挖了坑将她埋了,还给她烧了些纸钱,回去的路上,师傅一脚踩在一块石头上,石头一滚,人就摔倒了,伏在地上站不起来,再看,腿小骨断了,于是忙扶了他回去,闯江湖的总也知道自救的方法,几个人给他正了骨又绑了木板,派人去山上找了草药回来煎,走不了,只能在这里养伤。
第二天中午,村长来看他,聊了一会儿,村长说:“你们喜欢晚上练戏的哦?”
“晚上?不啊。”白师兄回答。
“可是,昨天晚上,半个村庄的人都听到有人在唱戏,就是从你们这儿传出去的。”村长认真的说。
众人对视,莫梅说:“我们很早就睡了,有人唱戏我们怎么没有听到?”
“是吗?昨天过了子时,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唱戏,你们也知道,这个村人少,天一黑就都关灯睡觉了,所以有什么声音也听得清楚,我还以为听错了,今天早上很多人都来问我,看来这不是错听,是有人唱戏,还是女声。”
“女声?”大家听了都转头看莫梅。
“不是我,当然不是,我要是唱了你们会不知道?”
拉二胡的师傅这时说:“梅子住在我隔壁,她要唱戏,谁还听不见?不是她。”
村长听他们一说,只是点点头,又坐了一会儿,便走了。
此事在每个人心里盘算着,而且也都猜出个八九分,除了戏儿,没有别人。
因此,大家都很沉默,纷纷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
下午,同村的女孩子来找莫梅,要带她上山挖野菜去,莫梅也正为没有东西吃发愁,这样一来自然很乐意。
她们挎着小筐向山上去,一路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只有莫梅笑不出来,心里总有什么东西堵着。
“莫姐姐,你的戏唱得真好,有空教教我们呗,将来等你们走了,我们好给村里的人解闷。”说话的小女孩子不过十二三岁。
她看看小女孩,她纯真的目光迎着她,很像当年的戏儿,在记忆里,她对戏儿不算很好,总是认为戏儿抢了她的地位,可是现在想想,那个孩子也是命苦,可是她又怎么去偷了师傅找回的宝贝呢?从前她没有这个毛病,别说宝贝,就是一个铜子放在她面前不让她拿,她都不会去碰一碰的。
她是早已知道师傅有刨坟盗墓的毛病,但每次师傅都会给他们买些衣料或是吃的,因此上她也懒得管那么多,难道戏儿也早就知道?
她恨这个师傅,也许她是想报复他?不对,如果那样,她一定会去告发他,只有一点,就是她想独吞,那晚是想趁机带了宝贝溜走的,对,一定没错,看不出来这个小丫头竟然比师傅还黑,比那两个师兄还狠,也许她死得并不冤枉呢。
想到这,她竟然有些释怀,不再为她的惨死而悲伤了,和那些小孩子们一起挖野菜,边教她们唱戏。
玩着跑着就进了山林,阳光被高大的树林摭得密不透风,只有几点阳光从树叶间透下来,一阵阵山风吹过,惊起一片枯叶,阴冷阴冷的。
莫梅发现了蘑菇就弯腰采着,不觉走远了,再抬头竟然不见了那些孩子,她大声地喊着她们,竟然没有人回应。
她四下看着泛着雾气的林子,分不清哪里是出林的路了,没有一丝声音,四周静极了,她甚至能听到自己慌乱的心跳声。
该往哪儿走?哪儿才是出林的路?她不知道,空气开始冷下来,也许天就要黑了,她不能就在这里站着等,于是她认定一条路走去。
沙沙沙,脚下,是枯叶碎裂的声音,每一步都是沙沙声,莫梅快步向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感觉似乎有人跟在后面,同样也有沙沙声,她停,声音没有了,走,声音又响起。
她只觉得头皮发乍,一股冷气从背后往上冒,于是她开口唱起来,一方面给自己壮胆,一方面也好让那些孩子听到,或者是附近有人,听了好来找她。
她的声音在林间回荡着,但是明显在发颤。就这样她边走边唱,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她突然停住了,因为她很清楚地听到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唱,她呆在原地,是的,她听出来了,那是戏儿的声音,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来,就像风从树根飞到树冠,又从树冠飞到地面,穿过每一棵树,穿过每一片叶子,在空气中飞舞,就像成千上万的尘埃包围着她,甚至穿过她的身体、她的每一根神经。
戏儿的声音连绵悠长,时远时近,唱时似乎还带着哭腔。
莫梅几乎要疯狂了,她丢掉手中的东西捂着耳朵向前疯跑,身后的声音追来,“师姐啊,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不是我害你的,别来找我。”莫梅大叫着,毕竟也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分不清方向,只是不顾一切地跑,等她跑不动的时候,她看见前面有个人影,有人了,她可以得救了。
于是她向那人影跑去,那人影看不去不紧不慢,却怎么样也追不上。接着她被树根绊倒了,怎么也站不起来,支着胳膊,抬起头来,看见前边是个小土包,落着些枯叶子,那人影不见了,四际只是茫茫的雾和荒草。
突然,她的心揪紧了,因为她看见那土包在动,像是有东西向外顶,土包裂了,向四外分开,然后一只手蓦地伸了出来,接着又是另一只,两只手攀着地面向上爬,于是,她看到了一个脑袋露了出来,拖着长发,一点一点地向外爬,她看清了,那正是戏儿,因为她认出了她身上的那件红衣服,宽袖子,下摆的串了红珠子的流苏,莫梅瞪大了眼睛,吓得动弹不得,戏儿向她爬过来,每爬一步,身下就是血。
“不,不,不要过来。”莫梅大喊一声这才想要跑,可是脚却不听使唤了,眼前的戏儿抬起了头,露出她发青的脸,额上一个大洞,正往外泊泊地流着血,流得一脸,她张着空洞的眼睛望向她,嘴里喃喃地说:“师姐,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眼里,流出两行暗红的血来。
她越爬越近,莫梅看见戏儿前襟的衣服敞开了,露出了一个空了的腹腔,内脏不见了,莫梅再也坚持不住,大叫一声,声音划破谧静的山林……
村民将莫梅抬回来时,其他人都是惊恐,因为他们看见的莫梅因受惊过度而扭曲的脸,眼睛向外突着,人,已经死去多时。
问那几个孩子,只是说一起挖野菜,本来还听着说话,转身人就没了,怎么也找不着,以为是先回去了,可是在林里找到了她丢了的筐,还有一支鞋,看样子是往山里去了,她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本来就要出林了怎么会又向山里去了呢。
更奇怪的是,人们是在戏儿的坟边找到她的,坟好好的,却不知道她到底看见了什么而被活活吓死。
莫梅的死让其他人很是吃惊,尤其是师傅和白、郑三人。
葬了莫梅,其他人开始慌乱,提出要离开。可是师傅的脚伤不好,只是说莫梅定是从山中摔了的,或是遇上了野兽。
莫梅死的第三天,村里一个放羊的半夜起来看见戏班子住的屋顶上有人在唱戏,穿着红色的上衣,吓得他躺在炕上不敢动。
而这次,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们听到戏儿晚上在屋顶上唱戏,唱得是窦娥冤,无比凄惨,令人毛骨悚然。
师傅让人找了桃枝,找了黑狗血来,还烧了纸钱,折腾了一天,心想,有这些避邪的东西在,料她也不会再来了。
傍晚时分,天开始下雨了,阴云压得很低,风呜咽着扫过屋顶,破烂的窗纸哗啦啦地响。
郑龙因为害怕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再加上外面风声雨声,更加让他无法入眠,突然,他听到一声叹息,分明得就是女声,似乎就在窗外,他咕噜一下坐起来,细细地听着,双眼紧紧望着门外。
一时间又没有了声息,顿了顿,他重新躺下,突然,又是一声抽泣。
他再次坐起来,蜷在墙角,紧紧地圈着被子。
那嘤嘤的哭声在雨中时断时续,郑龙大着胆子问了句:“谁,谁呀。”
外面没了声音,只是一阵阵的闪电将院子照得雪白。
过一会儿,又来了,外面就这样哭着,哭得郑师兄寒毛直立,不由地说:“是不是戏儿啊,我没害你,你别来找我,师兄知错了,师兄不该去盗墓,师兄以后再也不敢了,戏儿,你走吧,师兄知道你是个乖孩子,想要什么尽管说,现在别来害我啊,戏儿。”正说着,又一个闪电,他看见糊了白纸的门外面一片腥红,明显是一个人影!
郑龙紧紧地盯着,身子向后缩了缩,人影伸出手伏在了门上,哭声又开始了,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郑龙瞪大了眼睛,因为他看见有血从外面渗进来,先是五个手指印,接着就是是一团血喷在了门上,血印快速扩大着,哭声也逐渐疯狂,又一个闪电里,门被啪地推开,郑龙惊叫一声,他看见戏儿浑身是血地站在门外,大哭着向他伸出手来,“师兄,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啊。”
郑龙猛地将被子捂在头上,他的心在疯狂地跳动着,他不敢动,紧捂着耳朵不敢听,一盏茶的工夫,他才醒悟过来,外面除了雨声什么都没有了。
他鼓起勇气拔开一点缝向外看看,屋里什么都没有,门也关的好好的,门上干干净净,并没有血印。
难道是个梦吗?他喘息着,大大地呼了口气,这才一点一点地将被子掀开,是的,眼前一片宁静,他这才放下些心来,但心跳还是很快。
他松开被子角,慢慢躺下去,躺在枕上,盖好被子,手指却在身下触到了什么,湿湿的,手指间拈一拈,有些发粘,抬起手来往鼻下一放,闻到一股很重的血腥味。
他忽地坐起来掀开被子,又一个闪电,他看见整个炕上都是血,同时,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站在背后,他不敢回头,他已经感觉自己四肢在变冷,就这样坐着,就这样坚持着,他的心要跳出胸膛了,于是他猛地回了头,身后是满身血水的戏儿,青白的脸被湿了的头发粘着,一双黑洞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张着嘴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又一个坟包立在莫梅的坟边,所有的人都确定,这一切都是戏儿所为,师傅命令他们去买棺材,要厚葬戏儿,还要请法师超度她的灵魂,毕竟他也是怕戏儿来的那天。
棺材买来了,人们却立在戏儿的坟前呆立,坟已经被挖开,里面一片狼籍,泥土里只有那件红衣服,戏儿已经变成了一具被野兽啃食后的残肉白骨,留下的,还有一个有着青白脸色的头。师傅命人将戏儿的尸骨烧了,没有人敢去,无奈,只好将那件衣服挑进棺材里烧了,坟重新埋了土,草草了事。
等大家都回了四合院的时候才发现白威不见了,骡车也不见了,同时丢了的还有一些钱,显而易见,白威逃走了。
此时此刻,白威正驾着骡车飞快地赶路,莫梅死了,郑龙死了,下一个就是自己,只有离开,才能捡回一条命,只要能活着离开,以后一定要本本份份地做人,再不做挖坟盗墓的事了。
想到这,又加快一鞭向前赶。雨还在下着,似乎永远都不会停,两边高山耸立,风声啸啸,更是阴森。
白威看着路两边的景色,这应该是出村的路,可是为何却多了些林子来?白威一向都不会迷路,每次都是他打前阵,可是这次他却迷糊起来。
骡子也不确定地向前走着,又走了半个时辰,骡子停下了,白威怎么挥鞭它都不走了,无奈他只好下车,四处看看,而那骡子却转了头,拉着车飞快地跑开了,他追了好长一段路还是没有追上它,眼看着它消失在雨幕里。
还好,钱物在自己身上。
他转回头继续前进,路两边的树林多起来,几乎要阻了路,穿过一个小树林,前边没有山了,好了,终于离开那个该死的村子了,他暗自庆幸着,不由加快了脚步,心里竟然开始打算起日后的生活来了,身上的钱足够回乡做些小买卖的,赚了钱,再娶个媳妇,其实,他想跟师傅提亲,要娶莫梅的,虽然那丫头脾气急了些,倒还算长得标致,唉,谁又料到会出这样的事?如果不是戏儿那丫头,等离开这个村他就要向师傅提了,唉,算了,将来再娶个更好的吧,谁知道娶了莫梅将来会不会幸福,也许这是老天的安排吧。
正想着,就听到前边有人哭,抬头寻去,在一株树下,有个红影子背对着他哭得伤心。
他没有迟疑地走过去,渐渐发现那个穿件红衣服,矮的立领,宽袖,衣服下摆还有串了红珠子的流苏,这衣服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从哪里见过了。
“请问有事吗?怎么了?”他说着要去拍对方的肩膀。
可是那人慢慢地转过头却让他不由后退,他看见的是一张青白的脸。
“戏儿!”白威只觉喉部被哽住了,他以为他逃脱了,谁知道她还是跟了来,难道他非死在这儿吗?不,他不信,他转头就跑,拐个弯,他回头看看,是的,她没有追上来,他一定是把她给甩了,他吁出口气,继续往前走,看看天,已然转黑,阴云密布山林交错让他分不清方向。
他甩甩头,再抬起头时却看见一道红影在前边树下,不,不会是她。
但是他猜错了,戏儿,是戏儿,在前方等他!那哭声幽幽远远地缠着,他站定了,望着那红影,戏儿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活着就不怕她,死了又怕她什么。
他看看路边,捡到一根粗的树枝,紧紧地握在手里鼓着气向前走,走到戏儿身边,她慢慢转过那张青白的脸来望着他,哭声立即将他包着,他感到浑身发冷。
“我没有杀你,你为什么要缠着我?你还害死了你莫师姐,她虽然对你不好,总也是长辈,你害死她大逆不道!”白威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野里回荡着,戏儿哭着向他伸出手来,凄凄地说:“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我叫你再喊冤枉!”说着他举着树枝冲过去朝着她的头部挥过去,于是,戏儿的脑袋滚落一旁,身子也倒下了,白威很是高兴,一个小女孩,活着的时候就不怕她,死了也照样不怕她。
他笑着咽了口口水,又往前走。
天更深了,两侧却还是高的山,不算密的林子围在路的两边,雾升上来,他有些累了,便依着一棵树休息,身上倒走出了汗来。
突然,他听到那声熟悉的哭声,身上的汗立即变得冰冷。
他站直身体,竖着耳朵听,那哭声又没了,也许是神经过于紧张吧,他吐口气又依在了那棵树上,可是,哭声又来了,这次更清楚些,好象就在身边!
是的,在他的余光里,出现了一道红影,而且就在他的左边,他慌忙地握紧了手里的树枝,那红影转过身来,那青白的脸,流着暗红的泪,刚才明明把她的头也打下来了,白威有些胆寒地想,可是戏儿却依然向他伸出手来,凄凄地哭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白威举起树枝又一次用力挥下,戏儿的头滚落在地,白威转身就跑,这次是确定将她的头打掉了,不会再来了。
他跑得气喘,为什么还出不去?已经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到村口?也许,马上就能到了,马上就可以逃离这里了,他用衣袖擦擦汗,看看四周,一直不曾注意,这两边为什么还是高高的山,路边还是林子?而且情景如此眼熟,没有亮光,冷得厉害,他的脚步开始蹒跚起来,手里的树枝已成了他的拐杖。“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那哭声又来了,他全身寒毛直立,那声音就在四周。
“戏儿,我不怕你,我不怕你,你不过是个毛孩子,你不用吓我,我才不怕你。”白威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道红影闪过,转瞬间,便又在前边树下了。白威挥着树枝冲过去,脚下一绊,就摔倒了,一根被劈断的小树枝向着他的两眼之间迎来,脑子里他想起曾几何时,看见戏儿捡回来的小动物,每每当着她的面将动物的头活生生地砍下来,看着戏儿痛哭他无比快乐。“师兄,你快乐吗?你快乐吗?”耳边是戏儿的声音,越走越远,直到什么也听不到了。
白威找到了,是在戏儿的坟边,头被路边的一截树枝钉住,血流了一大片,人们还发现在坟的四周是他无数的脚印,不知他绕着戏儿的坟走了多少圈。
师傅让人去找车,准备马上走。
可是去的人没再回来,有人说是出了村了。这样,只把无法走路的师傅留在了村里,因为村里人总是听到这宅子里晚上有人唱戏,白天都不敢再来,空旷的院子里哪怕是在白天也显得万分诡异,只有师傅一人住着,其他人都离他而去了。
白天,他便坐在院子里发呆,晚上,瞪着眼睛听着屋顶上的戏儿唱,又怎么睡得着。
那声音就在四外的屋顶上不断地唱着。
也许是丑时了吧,声音没了,正待要睡,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小孩子的哭声。
他坐起来听,不是梦,是有孩子在哭,他下了床,柱着拐,往外一点一点地走,循着那哭声去了。
在厢房外,他侧耳听听,那哭声正是从那儿传来,于是他推门进去,哭声是从里间传出来的。这厢房何时有个里间了?没有多想,便进去了。
从里间的门缝往里看,一个小女孩,穿着件淡蓝色小花的,打着层层补丁的小袄正蹲在墙角哭,边哭边说:“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师傅,别打我,我害怕。呜呜呜——”师傅打开门走进去,那孩子不哭了,却一动不动地蹲着,师傅去拍她的肩,那孩子猛地转过头来,却是一张青白的脸,师傅吓得倒在地上用手捂了眼,可是,好一会儿,却是很安静,抬开手,发现自己是在炕上,难道是梦?他四处看看,是的,是梦,额上不禁渗出丝丝冷汗来,他叹口气重新躺好。
“师傅,师傅。”有人推他,张开眼睛,炕边坐着白威和郑龙。
“师傅,还不走?等会儿散场就不好下手了。”郑龙急急地说。
“干什么去?”师傅一脸茫然。
“您不是说有个财主的坟吗?”郑龙小声提醒他,扭头看看窗外。
“是啊,师傅,他们都在听戏呢,现在去正合适。”白威也低声说。
听听,外面正是锣鼓喧天,他坐起来,白威已经拿了鞋给他穿,于是他跟着他们两人从后窗跳窗走了。
山路很黑,郑龙在前边举着个小灯笼,三人匆匆地走,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坟边,他向四外看看没什么动静,便向身后的人说:“给我锄头!”说着往手心吐口口水,他拿着铁锄熟悉地刨着坟,不一会儿就看见了黑乎乎的棺材,身后又递来了撬棍,“嘎吱、嘎吱”地撬木头声音在漆黑的坟地里显得如此刺耳。
两三下,棺材撬开了,“拿灯来。”说着向身后一伸手,可是这次,身后却没了动静。
回头一看,郑龙和白威不见了,他跳进坟里用力地推开棺材盖,此时,云却淡了,惨白的月光照下来,他看见推开的棺材里放着的不是他所想象的宝贝,而是穿着一件红衣的戏儿!
他当即傻在那里。“师傅,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戏儿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他跳出坟墓往回跑,前边却看见有个人影正向他走来,跑近了,却看清来人是莫梅,莫梅瞪着往外突出的眼睛指着他说:“师傅,你背着戏儿干嘛?你背着戏儿干嘛?”他只觉头皮发麻,转身又跑,刚下山,看见路边蹲着一个人,不,一定不会是郑龙,可是就在他走近的时候,那人回头来,一脸的血:“师傅,你怎么背着戏儿?去哪儿?”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他一步不敢停,快要到家时,远远地看见白威正站在宅子门口看着他,双手正用力地拨着头上插着的一根树枝,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流了一脸,看见他远远地喊:“师傅,头好痒啊,师傅,你背着戏儿上哪儿去啊。”
他转身往村里去。
背后,只是戏儿嘻嘻地笑声,仿佛就在耳畔。
他不敢停,伤了的腿似乎是好了,他不及多想,只是跑。
远处有间房子,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开门啊,救我啊。”门吱吱地开了,里面漆黑一团,突然,从门里伸出一只手来卡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力地想将那只手掰开,可是却是徒劳的,那只手将他往屋里拖去,他拼命地挣扎着,转眼看见了脚边木桩上的斧子,他拿起斧子来向掐着自己的那只手用力地砍去。
突然,他眼前亮了,他看见四周有人,他认识,是马村长、村长媳妇,村长的儿子,村长的父母,他们围着自己,他用尽力气说话:“是我,是我挖的坟,不是戏儿,她是冤枉的,是冤枉的!”说完,便软下去再也没有张开眼睛。
村里人葬了师傅,他们每每想起这个戏班子无不觉得恐怖异常,每个人的死都是深藏玄机。
后来戏班子的人回来过,来时还带来了马车,可是,却空车而去,据那人说,当年莫梅怕戏儿来了抢了她的饭碗,曾经将戏儿带到很远的荒野里想将她丢掉,谁知过了一夜戏儿竟然又回来了,却什么都没说,却被师傅狠狠地鞭打了一顿,怀疑她企图逃跑。
郑龙也爱欺负她,一次将一盆鸡血从头到脚地淋在戏儿身上,然后把她关在一个有镜子的小黑屋里,从那时起戏儿就怕血。
白威师兄便想着办法让她见血。
因此,在戏儿小小的心灵里就恨着他们,而师傅却冤枉她。
村长告诉他,那天村长半夜来敲门,见了他们却发疯一般地挣扎着不进屋,最后竟然拿了斧子砍向自己的脖子,那么的用力,几个人都拦不住,斧子将脖子几乎砍断,却才说出了真相,还有想不明白的是他的腿明明是断了的,却不见拿拐杖,而且一路上有血脚印,曾寻去,正是从那被挖的坟处来的,而坟附近只是黄土茫茫,血从何来呢?这种种事情让人不可思议,一个戏班子便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散了,许是报应,不单单是一个戏儿,也许还有曾经被挖过的坟的主人吧……。
来人找到了师傅留下的一些钱,又开了戏班子,红红火火,而他自己也做了师傅。
“小玉,把那些旧的戏服浆洗浆洗,不说就不知道干活,整天就知道吃,洗不完不许吃饭,真是个懒丫头!”
“是的,师傅,师傅啊,这件红衣服是谁的,这宽袖子,这大红的牡丹,还有衣服下边还有红珠子呢,您看,真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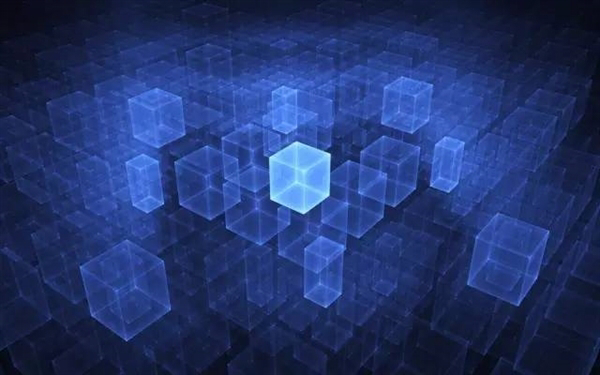








写小说的过分了吧,去小说网站还能挣个零花钱,怎么在这鱼目混珠
编辑能过说明是可以收的,你不喜欢可以绕行,我也没有赚你一毛钱对吧?记住我的名字,下次下风请绕道,可别浪费了您的宝贵时间哦
写的不错
谢谢捧场
写得太好啦,就是有点太悲情了哦,戏儿也太可怜了,哎
写的戏儿真是太可怜了呀,就这么冤死了,哎太悲情了
故事情节写得真是好呀,最后要是戏儿亲手杀死他们就更好啦
戏儿好可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