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一声紧一声地快速走来,我张开眼睛,似乎一直知道会有这脚步声一般,侧耳听听,果然是向我窗边走来的.
如预料之中,有人砰砰地拼命地砸着窗户,哪怕就是我这样醒着,也被他打雷般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呼地坐起来,瞪着漆黑的窗外,大声问:“谁啊?”没人应,外面没有月光。
再问,还是没人应,敲窗的声音也没了。
我发了会儿呆,然后又躺了,是梦?幻觉?等了等,还是一片宁静.
于是我闭上眼睛继续睡,朦朦胧胧地刚要睡,突然,又听到一阵脚步声,踩着碎石的那种,沙沙,沙沙,似乎还踢了一小块石头,咯啦啦地撞在墙上。
于是,窗户又一次被敲响了,我转过头,甚至能看见颤动的窗棂,”是谁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吗?”我问,可是,窗外却是死一般的安静。
我摸到枕下的火柴,哗地划亮并点燃了小柜儿上的一盏油灯,然后披衣下床,趿着鞋,举着油灯,小心翼翼地向窗边走去,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一动不动的窗,一双耳朵用力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甚至能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我伸出手,慢慢,慢慢向窗户靠近,突然,窗户被人从外面用力地啪一声推开,一张惨白的脸站在外面,被油灯笼罩着,我不由啊地惨叫一声,油灯也失手掉在地上,屋里立刻一片黑暗,我再抬头,窗外,却什么也没有了。
“川儿,干嘛呢?大半夜噼哩叭啦的?”我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被这样的突然说话,又吓得一声惊呼,转头一看,妈正披着外套掀着帘子望着我,我这才呼出一口气,抬手抹了抹渗出汗的额头,”咋啦?”她举着根蜡烛走过来,一脚踩上了碎玻璃,咯吱一声,她忙低头去看,然后又发现开着的窗。
“大冷天儿的,你开窗干啥?”我嗒然地坐在床沿上,这才觉得有些冷,妈准备走过去关上窗子,我忙喊住她,她回过头来疑惑地望着我。
“窗外,有,有东西。”我吞吞吐吐地说。
“有东西?啥东西?”她好奇地又向窗边走过去,我忙跳起来,站在她背后,谨慎地向外看,害怕那张脸又突然跳出来,我想,我一定会晕过去,可是,外面除了阵阵冷风,就是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
“是猫吧?”妈问着,又回头看我,可能发现我脸色苍白的样子不像说谎。
最近村里闹耗子,猫疯了般横冲直撞。
“也许,也许是吧。”我抓抓头,心里肯定不是猫,可是又说不清是什么,那张脸却清晰地在脑子里出现,不敢跟妈说,她一定说我是做噩梦了。
于是她伸手关上窗,用脚将地上的碎片向墙根踢了踢。
“做噩梦了吧?叫你别去听你四爷爷讲鬼故事,偏不听,快睡,以后不许去了。”果然。
她看我躺下,这才转身出去,不忘把蜡烛留在床头小柜儿上。
到天亮,也再没听到那声音。
第二天,我忍不住跑去跟我的好兄弟,小六子说了。
谁知,他说,他也做了同样的梦,我一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大太阳下,也觉得浑身发冷。
“走,去找根子,他最胆儿大,看他做这梦了没。”小六子说。
于是,我们一起向他家跑去,他爷爷说他上地儿干活去了。
远远就看见他跟他爸妈、他哥在地里捡柴禾,已经捡了小半车了。
我们远远喊了他一声,他直起腰来看看我们,然后跟他爸说了句什么,这才飞快地向我们跑来,边跑边拍身上的土。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走,上我家去,昨天我妈炒了一蓝子豆子。”我看看小六子,他扭过头,拍拍他的肩,“昨晚,你睡得好吗?”小六子问。
根子抬起头看看我俩:“头一挨枕头就着了,一觉到大天亮,怎么了?”
我跟小六子对视了一下,然后对他说:”我们俩可没睡好,都做了同样的可怕的梦。但是,又不像是梦,挺真实的。”我说。
于是,我们将事情跟他说了一遍,他突然笑起来,指着我俩笑的直不起腰来:“你们这两个笨蛋,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哈,哎哟,我肚子都笑疼了。”
他突然坐在路边大笑不止,弄得我们俩像个傻子一样看着他,“根子,你没事吧?”小六子用脚碰碰他的鞋。
“你吃错药了?”对于他这样的态度,我有些生气,我们吓成这样,他却那么开心。
“不,不是我吃错药了,哎哟,我说你们俩,快十五岁的人了,还被这个小把戏骗到,你们以为是遇见鬼了?哈哈,世上哪有鬼啊?都是四爷爷从书上看来骗你们的。而且,昨晚那个……不行,我不能说,我答应邵贵哥了,不能说的。”他摇摇头,捂着肚子,意犹未尽地还是呵呵地笑。
看着他我们成了两个丈二和尚。
“那我们问邵贵去。”说着我们转身要走。
“好好,我告诉你们吧,昨晚是邵贵出的主意,想要逗逗你们,以为你们会识破他,没成想,还真信了,你们两个笨蛋。”他指着我们又笑起来了。
啊?原来是他们在骗我们?
“根子,这很好玩吗?随便娱弄我们,当我们是傻子,你们很有意思吗?”我生气了,小六子的脸色也不好。
根子这才严肃起来,“好吧,算我们不对,其实都是邵贵的主意,其实并没有恶意的,就是他从城里的学校听说了一种新节日,叫什么万,什么节的,说是外国人的鬼节,所有熟悉的人相互吓,是表示感情深,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一招,没想把你们吓成什么样儿,不是想表示跟你们感情深吗?”
听着他这套说词,我跟小六子面面相觑。
“你们也别这样小心眼儿啊?大家都是好兄弟,为这点儿事你们就翻脸,太没情义了吧?早知道你们这么胆小,打死我们也不玩儿这个啊,算了,回头我跟邵贵哥说说,让他跟你们陪个不是。”
他的话一说完,我们反而觉得自己有些小题大作了,根子一向是个会说话的人,每次都能摆出一大堆的道理,“我们也不是生气,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节日啊,大家都是好兄弟,有什么陪不陪不是的?就是昨晚真吓了我们一跳。”
小六子上前拍拍根子的肩,于是我们又好了,跑去根子家吃炒豆子,然后又去找邵贵哥,在他家,我们看见了那张惨白的脸,是一个面具,还有假头发,邵贵哥说在他们学校,大多数人都买这个,然后拿着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四处跑着吓同学。
真不知道,这城里人怎么了,好玩这个?人吓人还不要吓死人啊?兴趣真是古怪。
我看着这个吓了我一跳的面具心想。
“邵贵哥,我家大门都锁了,你昨天是怎么进去的?”我将面具戴在头上,转脸问他。
“这还难得倒我?我上了你家房,然后用绳子绑着面具的头发,支在你窗外,然后用个大木头敲你的窗子,你这家伙,听到声音也不出来看看,害我差点从房上掉下去。”
原来是这样啊,邵贵哥真是够有精神的,大半夜不睡觉跑出来吓人,还怪我不出来。
在城里时间久了,精神有问题啊?
“对了,昨天下午我上后山逛了一圈,你们猜,我发现什么了。”他突然神神秘秘地说了句。
“什么?”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棺——材——!”他压低声音说着,脸上却出现了惊喜的笑容。
我们却瞪圆了眼睛。
“邵贵哥,后山就是祖坟区,你当然会在那儿发现棺材的啊。”小六子说。
“这我怎么不知道,可是那个棺材不同。”邵贵走到一边去给我们拿桔子汁。
“怎么不同?”我问。
他却没有回答我,只是垂了垂眼睛,然后笑嘻嘻地说:“想知道怎么不同?不如,今晚,咱们去一探究竟!”他话音未落,我们都本能地向后退了小半步。
他竟然乐开了:“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了,还怕这个?”他有些嘲笑地看着我们。
“不是的邵贵哥,我爸说了,那地方不能去,很邪的。”根子说。
“邪?唉,怕什么呀,我们血气方刚,顶天立地的,又没干过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而且这都什么社会了?你们还信鬼啊?鬼只是人们想像出来自己吓自己的。”被他这么一说,我们也一时没了主意,又不好拒绝,怕被人看成是胆小鬼,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吃过晚饭,我们准时等在村头的大槐树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邵贵哥拿着手电,昏暗的只能照到前边不远处的一小块地方,晚风冽冽,吹的身边的枯草干枝咯吱吱直响,我们一路顺着土路向后山缓缓走去。
月色当空,照得大地一片亮晃晃的,我们快要翻过小山梁,身上都出了汗,呼呼地喘着,再走不远,邵贵哥停了下来,用手电指着前边不远的一片林子说:“过了那片小林子,就到了,我们快点儿走。”于是他领先一步向前快步走去。
穿过小树林倒是没怎么费劲,就是一根小树枝把小六子的裤腿给挂破了,为此他还大惊小怪了一场,被邵贵哥训了几句。
又走了几分钟,我远远就看见在月光下发着青光的石碑,和一个个长满了荒草的小坟包,在这样的情景下,不禁感到一丝阴冷,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四爷爷讲过的坟地的女鬼的故事,现在,应该不会有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从某个坟包里爬出来吧,我想到这儿,竟然打了个冷颤,赶紧甩甩头,跟在邵贵哥后面继续向坟地深处走去。
“嘿,看见了吗?我说的那个棺材就在那儿。”顺着邵贵哥的手指的方向,我们都看见在最为开阔的地方,赫然停放着一具大棺材,不用走近也能看出是口红色的棺材,并且在四外还包着金边,只是,棺材上没有盖儿!
我们没有继续向前走,停在原地发呆,邵贵哥走了几步发现我们没有跟上,回过头来看着我们:”怎么了?走啊,都到这儿了,过去看看呗,怕了?是不是男人啊?”
我回头看看其他两个,他们抿抿嘴,就连平时自夸胆儿大的根子,也是犹犹豫豫地,磨讥了一会儿,我们这才继续向前走。
那口棺材很大,似乎是个双棺,我们很小心地向棺材靠近,邵贵哥站在棺材边望着我们,眼里放着光说:”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四个打赌,谁敢躺进这棺材里去,其他三个就请他吃一个星期的早点,咋样?”
我们都被他这个疯狂的想法赅住了,谁敢进去啊?我们三个相互对视后,都一齐摇了摇头,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邵贵哥呵呵一笑,骂我们这些人是胆小鬼,于是将手电递给我,说着不许反悔的话,然后双手支着棺材用力一撑,棺材摇了摇,他一腿就跨在了棺材沿上,另一条腿刚跨上去,就听他:“咦?”地说了一声。
本来我们就神经紧张,听他这一咦,都有些害怕,就想要跑,却听到邵贵哥的笑声。
“怎,怎么了,邵,邵贵哥?”我的声音很明显地在发抖。
“没什么。”此时,他已经跳进去了,声音从那棺材里传出来。
“只是这里面竟然还有一具骷髅呢,好像是女的。”天哪,邵贵哥,你到底有没有神经啊?有具骷髅你都笑得出来?根子在一旁紧张地说着。
“你们看!”他突然从里面站进来,在月光下,他真就像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鬼,半长的头发一扬一扬。
“什,什么啊?”根子的声音也比我利索不到哪儿去。“是个簪子,我说是个女的嘛,不过,这东西不值钱。”说着他又将东西丢回去。
“好了,你们看好了,我现在就要躺下了,你们数六十声,然后我再出来,不到六十声我出来也算我输。”
“邵贵哥,算了,我们服你,咱们还是走吧。”小六在一旁喊着。
可是,邵贵哥并没有听他的,还是执拗地躺了下去。
“一,二,三,四,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好了,邵贵哥,到了,你赢了,咱们走吧。”
根子冲那棺材大喊,等了半天,并没有听到邵贵哥站起来的声音。
“邵贵哥,别吓我们,我们回家吧。”我也大喊。
可是,依然没有邵贵哥的声音从那口棺材里传出来。
棺材一动不动地静静躺在空地上,月亮有些暗了,我抬起头看见一小片云正将月亮掩起来。
我顾不了许多,一咬牙冲了上去,可是,可是……我站在棺材边一动不动地看着里面。
“川儿,怎么了?”根子问我。
“是啊,小川哥,你说话呀。”他们边问着我,边向我走来,等他们走到棺材边的时候,跟我一样都呆呆地愣住了,因为里面根本没有邵贵哥的人影,就连他说的什么骷髅都没有。
棺材是空的,只有斑驳的漆皮。
我们三个慢慢地抬起头来,然后同时大叫一声转身就跑,惨叫声在林子上空盘旋着,显得更加恐怖。
我们一口气冲回村子,一眼看见我爸妈、小六子的爸妈和根子的全家人站在村口,另外还有几个人,他们远远看见我们都向我们涌上来。
“这么晚了,你们几个小兔崽子上哪儿了?”爸瞪着我怒吼。
“我,我们……”我低低头,这才发现手电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说啊!是不是去后山了?”小六子的爸用力地戳了一下他的头,小六子趔趄着差点摔倒。
“嗯。”他点点头,还是一脸惊恐。
“你们胆子不小,谁让你们去的?平时没跟你们说那种地方不许去吗?”是根子的爸。
“爸,我们也不想去,是邵贵哥叫我们去的。”根子仰起脸来看着他爸委屈地说。
“邵贵?胡说!人家好端端地在家里,别有事就往人家身上推!”
什么?我们三个立即对视,不可能,明明是他带我们去的!
“喂,你们三个真去了?”听到声音,邵贵哥正从人群背后挤进来,看见我们有些吃惊。
“邵贵哥!”我们三个又一次异口同声地看向他,眼睛瞪得老大。”
干嘛这样看着我?我白天只是说着玩儿的,谁知道你们真去了。”他好笑地看着我们仨。
“可是……”
“少废话,快回家去,看我怎么收拾你!”爸一揪我的耳朵。
我们三个就这样被大人们拎着耳朵拎回家了。
爸没打我,只是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让我以后不许去那种地方,会对祖先不敬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心里那个害怕,可是爸还不让我点灯,我只好用被子捂着头,脑子里只有那具空棺材,怎么也不明白邵贵哥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家的话,那么带我们一起去的是谁呢?
我不敢再想了,紧紧闭着眼睛,只想快快睡着,明天好去问问邵贵哥。
天刚麻麻亮,我就起床了,头疼得厉害,我发誓以后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听他们的了。
跟着爸去捡了些柴禾回来后又去用陈麦子换了新米,快中午时分才见小六子精神不济地来找我,说做了一整晚的噩梦,我们一起去找邵贵哥,在路上遇到了根子,他也是双眼充血。
还没到邵贵家,就看见他们家门外围着好些人,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议论什么。
刚到门口,邵贵哥的奶奶也正从门里出来,大家都围上去打听,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昨晚邵贵哥哭了一整晚,哭得很伤心,天刚亮才睡着,围着的这些人都是他们前后左右的邻居。
我们没法去看他,他奶奶只是坐在门外叹气。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也就散了,吃过午饭,我们再去,看见邵贵哥坐在门外看书,他看见我们很高兴。
“怎么才来?又睡到太阳晒屁股吧?”我们坐下后,他跑去拿了些炒棒花(用老玉米粒炒的食品)出来。
“邵贵哥,昨天……”我们刚要提,他忙将食指放在嘴前嘘嘘有声,示意我们别多嘴,不一会儿,他奶奶出去打牌了,我们这才进屋说话。
“昨天跟你们说完我就后悔了,本来想晚上跟你们说不去的,可是我到那儿以后,等了半天也没看见你们,我就拿着手电找你们去了,到了小山梁上,你们也知道,在那能看见小树林啊,可是我刚要下去,就看见在林子前有个人形似的东西发着光跳来跳去,我一害怕转身就跑,回了家还发抖呢,老实说,我以前从来不信这个的,可是亲眼看见了也害怕,心里还想你们一定不会去的,都是胆儿小的人,我不去你们也一定回家了,谁知道快半夜了,川儿他爸来我们家,我这才知道你们真的去了,正要找你们,你们却回来了,好歹没出事,我心也安稳了。没看见什么可怕的事吧,当然了,看见你们能安全回来也应该没出大事。”
他往嘴里放进一把捧花,咯吱咯吱地吃个香,我们真不知道该不该把昨晚的事全都告诉他。
“邵贵哥,那你昨晚哭什么啊?”根子问他。
“哭?”邵贵哥突然停住,“我什么时候哭了?”他完全不知道。
“今天早上,我们来找你,你们家门口围着好些人,问你奶奶怎么了,她说你昨晚哭了一夜,你奶奶也不知道,只是说天亮的时候你才睡着。”听我们一说完,他立时呆住了,眼睛望着墙角。
“我哭?不知道,我只是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女人,站在我屋里,在梦里感觉我跟她很熟,我听她说话,心里就难过,可是她说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
“什么样的女人?”我问。
“个头不高,很瘦,头发盘着,用一根发簪别着,身上穿一件大红的衣服,就是旧社会的人穿的那种,有小立领,袖口这么宽。”他在自己腕处比划着一尺宽的距离。“衣服前襟还有绣上去的大牡丹花,衣服下摆是一排串了红珠子的流苏,样子挺可怜的。”
“是不是一根有绿珠子的那种发簪?”小六子突然问。
邵贵哥想了想,说:“好像是吧。”
“那跟你从那棺材里拿出来的一样喽。”我们都飞快地看向小六子,他自觉说错了话,忙一捂嘴。
“什么棺材?”邵贵哥问。
我们沉默不语。
“说啊,什么棺材?”还是不要瞒他了,事情比较严重,我这样觉得,然后舔了舔嘴唇将昨晚的事情一点不漏地告诉了他,听完,他的脸色就白了。
“不可能!我昨天明明是在家的,跟你们在一起的不是我,绝不是。”从邵贵哥家出来时,他还是很沉闷的样子,我们一路上也没有说话,各回了各的家,吃饭,睡觉。
哭声?是的,是哭声,远远的,若隐或现的。
我张开眼睛,扭头看着窗外白色的月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而那哭声也随着月光飘了进来,哭声像寒风一样在这寂静的夜色中一点点散开,飘进每个缝隙里,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呜呜的风,可是,那不是风,那的确是哭声,空灵的却又沉闷的,让人一乎儿觉得似乎是自家的屋顶,甚至窗外,一乎儿又像是在村外的山林里,甚至更远的地方,总之,无论在哪儿,都能让人听得见,外屋亮起了光,我听到爸妈的说话声,他们也听到了这声音,所以我更加肯定这不是梦,是真实存在的!
我僵在床上,听着那凄惨的哭声不敢动,外屋是爸穿鞋的动静,我这才下了地,推开窗户,看见爸走出屋,在院子里怔了怔。
“爸,什么声音?”我轻声问,似乎是怕惊着那个恸哭的人,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一张悲惨的表情。
他冲我摇摇头,然后走向大门。
我忙穿好衣服跟鞋也跑出去,爸已经站在院外了,我看见有不少人都站在自家院门外侧耳听着,那声音只让人浑身发冷,有狗开始狂吠,那哭声突然停止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从那以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那哭声就响起了,每次的时间都在加长,我不再出门眺望,紧紧蜷在被子里动也不敢动。
第四天,村里有个小孩子死了。
死状可怖,大张着眼睛,脸都变形了,一大早起来发现已经没了呼吸,一家人哭天抢地,却再也唤不醒自己宝贝的孩子,一个七岁的活泼可爱的男孩儿。
夜里,哭声还在继续,天亮,一个老头儿死了,跟那孩子死状一样,无病无伤,只是徒劳地张着一双眼睛。
村里开始慌乱,不知道下一个死的人是谁,人们开始围攻邵贵哥的家,因为人们很清楚地听到那哭声就是邵贵哥!虽然我们不肯相信,但的的确确,是他的声音!我们从他家后墙翻进去,他用一脸的无辜跟苍白回答我们,他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每晚,都有那个女人来,有时给他唱小曲,有时给他跳舞,对于哭,他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们该怎么做?邵贵哥说他只能离开,他走的那天下了雨,有家人在办丧事,这次死的是个村里买猪肉的大叔,身体跟铁一样坚实。
邵贵哥回城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午夜来时,那哭声又来了,这是第六天,死了三个人。
村里有人开始搬家,大部分还是要留在村子里的,穷人的窝,能去哪里再安家?
这下,没有人再说邵贵哥了,却被深深恐惧包围着,谁也无法解释这哭声打哪儿来,后来,村里一个老头儿想起我们曾误闯祖坟地,怀疑是不是触怒了祖宗,而受到了惩罚。
于是,全村人开始进行烧纸的祭奠活动,大白天的,村子里香烟弥漫,四处都是纸灰飞扬,气氛更加阴晦起来。
第七天,村里安安静静的,所有的人都在惊愕中没有回醒,包括我在内,因为所见之处,所有的鸡鸭猪羊狗兔牛,一夜之间,全死了,墙角、路边、树根、圈里圈外全是这些动物的尸体,张着眼睛!
老人们说,诅咒来了,那些闯了祖坟的孩子惹恼了祖宗,他们下了诅咒,全村人都要死了!
是这样吗?当这样的话传进我们三个人的耳朵的时候,心里突然像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恐惧,这么说来,我们也会难逃一死,在恐惧中,我们相对无言。
天刚黑,爸跟妈就把我送出村外,村民已经开始迁怒我们,谁也说不上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能逃。
黑漆漆的路上,我们三个没命地跑,一刻也不停止,眼里的泪也没有断过,洒了一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要逃离自己的家,把死亡留给自己的亲人,也许将来我会恨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可是我没有选择,只有逃,逃……
当我们再也跑不动的时候,就找了个隐匿的地方睡觉。
半夜,根子推醒了我们,他指着我们来时的路说:“看,那群红衣服的人,他们来找我们了。”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漆黑的路上,哪有半个人影?
“根子,哪有人?”小六子也这样说。
“你们看不见吗?十来个红衣服的人,没有脚,没有脸,他们来了,来了啊。”他的脸开始因为惊吓而扭曲,我们拼命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可是他大张着眼睛指着来时的路,一点点倒下去,然后,剩下一副躯壳,他,死了。
诅咒没有放过我们,终于追上来了。
虽然我没有看见根子所看见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也离死亡不远了,甚至就在身边。
小六子痛哭失声,为了根子,这个十几年的朋友,也为了自己。
“小六子,咱们不跑了,咱们背根子回家,不能把他丢在这儿,要死,也要跟家人在一起。”我说,他含泪用力地点点头。
于是,我背着根子,转身向村子走去,死就死吧,总比见不着自己最亲的人好。
可是,眼前的路却突然弯弯曲曲的,那些树都突然像折断一样弯下腰,从树干里忽然地就挤出一张张脸来,那些树枝像一双双手,向我抓来,地面也出现了一个个的人头,哭声,又来了。
“小六子,时候到了。”我说。回过头,小六子不见了,四处都不见他。
“小六子——你在哪儿——”我虚弱的声音没有得到一声回答,四下那些手都没有了,又成了平坦坦的路,天将明,突然,我听到背上根子在笑,很细的声音,像个女人!我低低头,却看见垂在胸前的根子黑色的衣服袖子,变成了红色的,一双白嫩的手一甩一甩地。
我只觉得自己头发全都立了起来,脖子处,一摞头发眼看着越来越长,垂在地上,而胸前那双手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立刻无法呼吸,而那些头发也紧紧缠住我,眼前一片黑暗,一股血腥与恶臭包围着我,冲进我的鼻孔,哪怕我用力抵抗,还是没有办法挣脱死亡的脚步声,沙沙,沙沙,还有那笑声,跟那哭声一起传来,越来越冷,越来越无知无觉。
一道刺眼的白光猛地射在我突然张开的眼睛上,使我又一次闭起来。
“小川哥,小川哥!”有人叫我,是小六子。
我张开眼睛,是的,是小六子,他蹲在我身边看着我,我一把抱住他,喜极而泣地说:“呵呵,小六子,你没死?太好了,我也没死吗?还是我们都……”
他推开我一脸愁容地说:“别胡说了,我们都好好的,只有根子哥他……”
他看向我的另一边,我扭过脸,看见一个白色床单,下面似乎是一个人形。
我猛地坐起来,却有什么东西让我的胳膊刺痛。
“唉,别动啊。”我转头看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白衣服,正在给我打针。
我这才发现,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戴着口罩,熟悉的眼睛盯着我。
“邵贵哥!”我说。
他点点头。“那是,根子哥吗?”我指着那个白床单下的人问。
他回头看了看,沉重地点了点头:“是的,是他,救不活了。”
有两个人将盖着白床单的根子哥抬上路中央的一辆救护车,然后邵贵哥将我扶起来。
“觉得怎么样?”我点点头,虽然还是有些晕沉沉的,感觉却好多了。
一个月后,我们剩下的人回了村子。
这个村子不再是以前那个了,而是被搬到另一个更为开阔的地方,远离那片坟地,因为邵贵哥告诉我们,那片坟场有很严重的沼气与尸腐毒,长年累月地影响着村民的生活,只是并不严重,前几个月,那片地发生了地壳变动,再加上多风的季节,所以村民很快被感染,抵抗力微弱的人就猝死了,从而引起了诸多令人恐怖的事件,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包括他自己在内,每夜的哭声只是地壳运动造成的一种响动罢了。
好了,夜哭郎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其实世上有些东西如果抛去想象,本质是很容易解释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毕竟这个世上会有各种事情发生,谁又能一一解释那些不可思议的怪异的东西呢?
比如说,当我搬了家后在我的小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有绿珠子的簪子,而在邵贵哥的衣箱里无故多出来的那件红色有绣花牡丹的宽袖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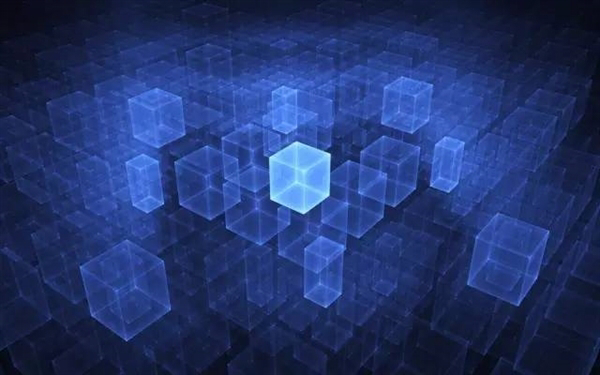



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