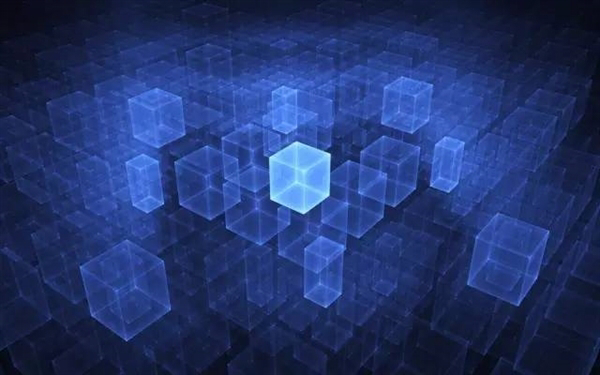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 (三)恩怨
张发祥叹了口气,语重心长的说道:“姐啊,不是当弟弟的我不在意你,实在是有些事情你也不能看表面。彭友邻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不学无术,其实背地里温柔着呢,他无父无母,也没有累赘,你跟着他过不但轻巧,还能帮衬帮衬家里不是?”
张玉凤觉得自己的弟弟是那么的陌生,她不敢相信这是弟弟能说出来的话。
可是张发祥接下来的话却让张玉凤寒毛直竖,吓得连连后退,缩进了母亲的怀里,抖得不成样子。
“我知道你想离开这里,可是你也不想想你才是初中毕业,出去能干些什么呢?况且你不在家里,谁能照看父母呢?”
“你……怎么会知道我想离开?”
张玉凤忽然想起自己离开的这件事只跟张发祥说过,是啊,她怎么不想想,怎么就那么巧,在自己离开的深夜会碰上一个整天混迹在赌场里,不愿意回村子的人呢?怎么会就那么的巧!!!
“是你!是你告诉的彭友邻,是你!”
张发祥不置可否,只是嘴角勾起一丝轻蔑的笑,说道:“时间有些晚了,我先休息了,姐,你好好考虑吧。”
张玉凤猛地从炕上站了起来,光着脚就要下地去追张发祥,她嘴里大喊着:“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回来啊!”
可是母亲一把抱住了她,她不可置信的低下头,母亲泪流满面,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脑袋一下子晕晕乎乎的,粗喘着气,大声喊道:“是他,是他干的,妈!他让人强暴我!是他!张发祥,我要杀了你!你不是个东西……”
张玉凤哭的撕心裂肺,当她得知她不能去上高中的时候她没有哭成这个样子,当她被彭友邻欺侮的时候她没有哭成这个样子,可是当她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弟弟的默许之下时,她崩溃了。
她的心理防线彻底的崩塌了。
她几乎是嘶吼道:“我要去报警!我要让你和那畜生都去坐牢!我要……”
就在这时,沉默已久的张奇森狠狠打了张玉凤一个巴掌,说道:“你敢!你还有没有心,那是你弟弟!”
张玉凤被这一巴掌打蒙了,嘴里说着:“他不是我弟弟。”
张玉凤还是嫁给了彭友邻,一个混混儿,一个赌徒,一个酒鬼,喝醉后还会打她。
她一时的噩梦变成了一世的噩梦。
张玉凤恨啊,她恨这不公平的命运,她恨只想着弟弟的父母,她恨毁了自己一生的彭友邻,她最恨的是张发祥。
张玉凤从彭友邻嘴里拼出了事情的全貌。
张发祥想去城里定居,可他不想带上没文化的父母,又不想被人说自己不孝,所以自己这个可有可无的姐姐必然得留在村子里,永远不要出去。而彭友邻缺一个妻子,缺一个被他压榨的赚钱工具和生孩子机器,两个人一拍即合。
张玉凤会厌恶张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虽然张明只是张发祥的私生子。
张发祥听从父母的介绍娶了隔壁村的女孩儿,因年龄不够,二人只是摆了酒席,却没领证。
因此在张发祥去了城里念书,并且在女孩儿生完孩子以后,表示自己和同学领证的时候,女孩儿便扔下三个月的张明离开了。
张发祥从没跟城里的妻子说过,自己还有个孩子。
所以,张明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
张明长得很像张发祥,张玉凤每次看见张明的时候都想弄死张明,可杀人犯法,她不想铤而走险,况且真要杀的话,也得杀张发祥,不然岂不是亏了。
在张玉凤给彭友邻生了第二个孩子彭子龙以后,彭友邻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了,十几年不回来,大家也都当做他死了。
张玉凤不喜欢彭毓红和彭子龙,她为什么要喜欢强奸犯的孩子?把他们生下来就已经是罪过了。
但是,张玉凤也还是自己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了。
她对彭毓红和彭子龙的感情复杂极了。
因此,她把彭毓红嫁给了老头,因此,彭子龙死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现的那么伤心。
警察也是刚刚调到这里的大学生,哪里知道村子里这些个弯弯绕。
被张玉凤缠的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去张明家,再问一问。
- (四)纸人
警察名叫王庆历,因着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大二的时候入伍,当了两年兵,退役后考取了选调生,才来到县城里当了警察。
说白了县城里警察的这个职位只是他的一个踏板,国家对退役军人照顾,但也要循序渐进的,他怎么也要在这穷乡僻壤的带上个一年半载,才能调回地级城市去。
若是旁人有这种情况,早就捧着铁饭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耽误自己晋升,才不会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尤其是农村妇女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
但王庆历这人却是个死心眼,他想着这毕竟是条人命,总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定了案,怎么也要照顾照顾家属的心情。
于是王庆历跟着张玉凤向张明的家里走去。
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低矮的房子挡不住落日的余晖,不知名的鸟发出奇怪的叫声。
夕阳没了温度,让人觉得身上冷冰冰的,风一吹过,王庆历紧了紧衣服,总觉得这边的黄昏更冷一些。
张玉凤看王庆历的样子,嘴角撇了撇,却也没说什么。
苦难和不堪早就打不倒这个女人了,何况是微凉的风。
可张玉凤心里也藏着秘密,可怕的、能吞没一切的秘密。让她感觉寒冷的从来不是风,而是内心深处的秘密。
走着走着,张玉凤忽然停下了脚步,王庆历困惑的看着这个比自己矮了整整一头的妇女。
她的脸上满是皱纹,黝黑的皮肤上带着皲裂的死皮,她的牙齿泛着黄光,一开一合间,说道:“警察同志,其实张明有点邪乎,他是配阴亲的。”
“配阴亲?”王庆历知道这个词,可是当听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本正经的说出来的时候,心里难免感觉到违和,他皱着眉,眼中的不解刺破空气。
张玉凤低下头,闷声说道:“您别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存不存在的不好说,但怎么也算是给活着的人一个念想不是?”
王庆历勉强的点了点头,右手的拇指放在食指上蹭了蹭,他有一点不安。
“我跟您说这个可不是为了别的,实在是配阴亲这个行当有诸多的禁忌,包括他屋子里的东西也有不少说法,您信不信的无所谓,就当个风俗看待也行……”
随即,张玉凤踮起脚尖,凑到王庆历耳边低声说道:“他屋子里的东西,您一样也不能动!”
张玉凤的呼吸打在王庆历的耳朵上,王庆历觉得耳朵有点儿痒,这可不是妙龄少女给情哥哥带来的痒,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带着黑暗和疼痛的麻痒,这股麻痒顺着王庆历的耳朵传遍全身,他打了个哆嗦,沉默的点着头。
配阴亲?
真是个奇怪的词。
活着的人说是为了死人好,要把不认识的两位结合到一起,这和封建时期的包办婚姻有什么区别?这种只是给活人创造一个心安的活动到底有什么意义?若是真的有鬼魂的存在,它们恐怕也会觉得哭笑不得吧。
可本着尊重当地习俗的心情,王庆历还是答应了张玉凤的要求。
王庆历跟着张玉凤到张明家的时候,张明正在给纸人画脸。
张明的动作很快,朱砂笔一勾一挑,眉毛、耳朵、鼻子和嘴就成了型,唯独没有眼睛。
白花花的纸上,印着红艳艳的嘴唇,在有些昏暗的屋子里显得鬼气森森。
王庆历搓了搓手指,总觉得屋子里比外面还要阴冷一些。
张明见他们来了,眼皮都没抬,反而继续手里的活儿。
不消片刻,十个纸人便画好了。
张明缓缓的放下笔,原本挺直的脊背一下子弯了下来,仿佛筋疲力尽。
他从里屋拿出来三个小凳子。
说是凳子,称为交叉更为贴切,就是那种两片木头,中间穿有宽带子的凳子。
很小很矮,又散发着古老的气息,不知道用了多久。
王庆历看着这破旧的凳子和凳子旁边的纸人,下意识的咽了口唾沫。
但还是走了过去,在张明的示意下坐在了凳子上。
这个凳子对于一米八的王庆历着实有些小了,他的腿卷缩着,整个人都不舒服。
“警官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吗?”张明的身上穿着白色的衬衫,上面沾着红色的朱砂,朱砂星星点点的散落在衬衫上,那种艳丽的红色比血迹还像血迹。
张明长得浓眉大眼,脸颊轮廓是那种国字脸,整个人看起来正义凛然,他神色镇定。
可是他的神色越镇定就越显得他衬衫上的红色妖异。
妖异顺着夕阳的余晖一寸寸的上升,勾缠着张明的发丝,然后消散在空气中。
王庆历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只觉得莫名的熟悉,这个场景自己似乎见过?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王庆历这话一出,张明还没什么反应呢,张玉凤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道:“张明,我就是想问问你,我儿子出事那天,你在干什么?”
王庆历没有打断张玉凤,仍旧观察着张明。
“上次警察来的时候就问过了,但是我……可以再说一遍的,姑姑。”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姑姑这两个字张明着重的说了一下。
张玉凤咬了咬牙,瞪着张明,却也没反驳。
“那天,东赵家沟的赵芳找我给她的女儿配阴亲,当时她就在我家,我们聊了一天,你可以去找赵芳问问……”
“你给赵芸芸找的谁?”张玉凤问道。
“这属于顾客的隐私,我不能说。”张明缩了缩脖子,好声好气的回答道。他这动作与他棱角分明的脸实在不搭,但看起来就像个面对警察畏畏缩缩的庄稼汉。
“你是不是把子龙配给她了?你这个丧良心的,敢用活人生魂配阴亲,你不得好死!我是对你不好,可子龙一直把你当兄弟,你忘了你有一年差点饿死,还是子龙拿了粮食才把你救回来的吗?”
张玉凤说着就要去打张明,却被王庆历一把拦住,劝慰道:“张大婶你也别着急,咱们再问问,再问问看啊……”
张玉凤对警察还是敬畏的,登时坐了回去,看也不看张明一眼。
“张大婶怀疑你用……彭子龙的灵魂给人……配阴亲,你想说什么?”
“您可能是不知道,配阴亲最忌用生魂,否则轻则残废,重则死亡,我怎么敢用人生魂?姑姑不知从哪里听说的这邪门歪道,我知道姑姑不喜欢我,但她毕竟是我姑姑,而且表弟也同我玩的不错,甚至还救了我一命,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害他?”
张明说话慢吞吞的,说到后来语气中还有三分焦急五分悲哀:“警官,您要是实在怀疑我,就带我去警察局吧,我全面接受调查,只要能查清楚子龙的情况,我怎样都可以!”
张明说着还激动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的对着张玉凤说道:“姑姑,你也别太伤心了,若是……若是子龙还在,一定也不愿意看见你这样。子龙不在了,还有红、彭毓红呢,你以后的日子等着享福吧。你想想你要是伤心过度,弄坏了身子,多不值得啊!”
张明这段话说的有理有据,不仅带着逻辑还十分凄切,王庆历听了都觉得这只是一位为了姑姑着想,却遭姑姑厌弃的淳朴之人。
张玉凤听着张明字字关心的话,冷笑一声,说道:“小兔崽子,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暗地里干的那些勾当,警官,你可不能听他装可怜,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周先生死的不明不白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张玉凤这话一出,张明的神色微变,眉毛微微皱起,看向张玉凤的眼神里带了泪水,整张脸都气红了,说道:“姑姑,你……你可不能当着警官的面说……说这个,周先生是我的师傅,他去世了,我最难受了,你说我可以,就是不能说我师傅!”
张明说着就举起了拳头,眼看着就要向张玉凤砸去,坐在一旁的王庆历猛地站了起来,小小的凳子倒在地上转了好几圈儿才停下。
“你想干什么?!”王庆历大喝一声,同时冲到张明近前,架住了他的胳膊,一翻一扭就把他按在了地上。
王庆历毕竟是年轻,并不知道这样做带来的后果,若今天来的是个老警察,绝不会像他这样,在张明还没动手的时候就把他按在了地上,这么做很容易被群众举报的。
张明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半天没了动静。
王庆历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太用力了,张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是当他缓缓放开张明的时候,张明却没有起来,反而就势躺在了地上,王庆历一看,发现他满脸的泪水,嘴唇抿得死紧,耳朵尖都是红的。
张明低沉的、颤抖的、无声的哭泣,让人看着如此的揪心。
他的嘴里小声的说着:“不许你这么说……”
王庆历心里一下子就不得劲了,颇有些不好意思的想扶张明起来。
一旁的张玉凤脸上露出讥诮的神色,说道:“真能装,被我说中了,所以才恼羞成怒的吧……”
张明对着地面的那半张脸扭曲着,被地面磨得破了皮,可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反而开口说道:“元年五月,婴儿坟冢,婚丧嫁娶,自有天命……”
张玉凤一听这个话,瞬间变了神色,她咬紧了牙,怨恨的看着张明,眼神里还带着些惊惧。
她怎么忘了,张明是给人配阴亲的,总能比活人知道更多的秘密。
那……张明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周围的十个纸人直直的站着,靠着墙整齐的一排,它们全都没有眼睛,张玉凤却觉得它们的眉毛似乎和张明刚画上的时候不太一样。
这些纸人似乎对这场闹剧感到厌烦,于是它们皱起了眉头,它们想,这群人真奇怪,怎么有眼睛?
纸人对于人来说只是纸,但是纸人对于心里有鬼的人来说却是鬼怪。
张玉凤心里就有鬼。
所以在这一刻,张玉凤突然不想跟张明作对了。
自己该去报复张发祥才对,至于张明,就随他去吧。
张玉凤绝对不承认是因为她害怕了,害怕张明真的知道些什么。
张玉凤跟着王庆历从张明家出来的时候,整个人木愣愣的,仿佛丢了魂儿,她看着王庆历一张一合的嘴,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张玉凤满脑子都是,张明怎么会知道婴儿坟冢?!
也许他不知道,只是随便说的呢?
王庆历看着失魂落魄的张玉凤,心里觉得怪怪的。
在来张明家之前,他以为张玉凤可怜极了,女儿远嫁,儿子溺亡,不能接受事实很正常。
可见到张明以后,王庆历却觉得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了。
张明表现的很完美,仿佛是一个被姑姑长期欺负和编排的窝囊废,缩着脖子的样子看起来畏畏缩缩。
但也正是这份完美,使得违和感愈发浓烈。
一个胆小的、不善言辞的懦夫,居然能面不改色的画纸人的脸,居然敢给人配阴亲,最吊诡的是,张明的所有说辞全都逻辑通顺,句句在理,把自己完全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
真正不善言辞和腼腆的人遇见这种情况大概会憋红了脸,说不出话。
而张明却像是经过无数次排练一样,已经没了排练的痕迹。
疑惑在王庆历的心里扎了根,可这疑惑来的毫无根据,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王庆历告别了张玉凤,临走前还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笑容。
微凉的风吹过,夕阳的余晖洒在王庆历的身上,他露出一口白牙,笑的灿烂,他说:“您别着急!我肯定会调查清楚地!”
王庆历决定第二天要去东赵家沟问问。
当张玉凤和王庆历离开后,张明脸上的红色迅速退去,整个人变得面无表情。
他在院子里接了一大盆水,在里面放上洗衣粉,用手搅得出了泡沫后,开始刷凳子—-张玉凤和王庆历坐过的那两个,然后开始擦地。
地上还残存着他擦破脸的时候的血迹。
张明去了里屋,从上锁的小抽屉里取出一支细细的毛笔。
这支毛笔很小很细,看起来和普通毛笔没什么两样,大概唯一的区别是,这是用人的毛发做的笔。
张明小心的用笔沾了沾地上的血,然后用这支笔开始给纸人画眼睛。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昏暗的灯光照不清张明的脸,也照不清纸人的脸。
笔上很快就没了血迹。
张明低垂着眼睛,张开了嘴巴,他的牙齿异常锋利,一口咬在了自己的胳膊上,鲜血“汩汩”的冒了出来。
张明看着流出来的血,笑了起来。
他的笑很奇怪,他笑的前仰后合,眼泪都下来了,偏偏一点儿的喘息声都没有。
嘘!听!仔细的听!
好像连呼吸声都很微弱!
就在这时,一声叹息传来,张明一下子停住了笑意,开始给纸人画眼睛。
夜,黑漆漆的,没有月亮,屋子里只有张明和十个纸人。
那么你猜,张明笑的时候是谁在叹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