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我又在这里敲响了键盘。不在的那段日子,我并未离开,只是一直在回味我所经历过的,回想认识的老人家和我说的,朋友告诉我的……我想把这些事组织成文字,然后再表述给大家,内容可能天马行空,也可能不切实际,还请各位姑妄听之。
我以前住在农村,那乡下有着一望无际的田野,春夏天绿油油,生机盎然,但秋冬时候则会略显萧条,正如我码字的这档口。
邻村有个比我稍大的姑娘,我叫她玉儿姐,现在的我已经记不得是怎样和她相识的了,但印象中她却是真真切切的十分照顾我,放学时候她经常帮我拎着饭盒,早上也会在那地方等我一起走。
每每想起,似乎童年的时光近在眼前,我很感谢生活一直在波澜不惊的给着我惊喜和余味。好了,铺垫结束,今天要讲的事就是玉儿姐告诉我的。
深秋时候的一天傍晚,我放了学,和玉儿姐走在回家路上。今天的她不似往活泼,步伐中透露着一点漫不经心,俩人的聊天说话也断断续续。
我从小心思比较细,从和她同村的同学那边大概已经了解到是她的某个亲人离世了,最近这两天正在操办后事,我很想表达出大人般的关心,但是毕竟年纪小,安慰的话却说不出几句,到嘴边只憋出来一句:“姐,你今天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呀?”
她边走边侧过脸来,皱着眉头看着我说:“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重的油漆味道?”
我听罢使劲深呼吸了几下,清秋的冷风一下子灌进了我的肺里,我禁不住的几声咳,呛红着脸摇摇头,支吾了一句没有呀。
玉儿姐听我说完,又回头看向了路,说了一句:“哦,我总能闻到一股奇怪又刺鼻的油漆味道,和你们说了,大家却都不信。”
话止于此,再往下却是什么也不再说了。
第二天早上,我没在路口看到玉儿姐,心里老大的失落,心想可能是我昨天说错了什么话了,又或者是她今天去了那个亲人家里,总之,她不开心。
等再见到玉儿姐的时候,是在半个月以后了,放学时候,她又来带我一起走了,我满心欢喜的跟在她身边,说着最近我遇到的事,她却不答话,只静静的听。
走到大坝桥的附近,她坐上了坝边的一块平石,我也跟着坐在了旁边,这时候她托着腮,看着天边山头上逐渐变红的太阳,轻悠悠颤颤的说了一句:“小赟,我好像遇到了鬼。”
年纪尚小的我不知如何答话,只哦了一声,玉儿姐似乎也不在意我如何回答,自顾自的讲了起来:“那个已死去的人是我的远房亲戚,我要喊她舅妈,前几天我跟着爸妈去了她家,灵堂你也知道,白花花的布,红通通的假人,你真哭两声,我哀嚎几遍,唢呐再响一阵,似乎气氛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骨子里不喜欢这种感觉,心想磕完头就出去吧。低下头的时候,我能看到地上铺的黄稻草,光线照再上面就有一些张牙舞爪的碎影,零零乱乱;面前供桌上的蜡烛光,忽大忽小,不经意间就会一阵抖动,甚至还能听到轻微的噼啪声;桌上摆放的供品,不生不熟的散发着一阵阵的肥腻味道;往后是一对纸扎的人,做工粗糙,假人脸上刷着粉红色,怎么看怎么奇怪,毛笔画的弯眉毛,细细的眼,上翘的嘴角,好像随时都能笑出来,这让我不敢对视;吊着燃烧的盘香,有种特有的味道,不像庙里的檀香,也不像坟上的黄香,让我头晕脑胀;透过中堂的纱帐,隐隐约约能看到一口棺材,厚重的木板拼接再一起,刷着暗红色的漆,透着肃穆,放置在两张条凳上,棺材底倒扣着一只篮子,里面一盏油灯不紧不慢的发着昏黄的光,篮子上面有一双逝者生前的鞋,是很普通的一双鞋。”
“跪拜完我就站起来,跟着爸妈去搀扶棺材旁回拜着的家属,刚卷起纱帐,一股刺鼻的油漆味立马冲进了我的鼻腔,这气味迅猛又恶毒,随即像是传遍了全身,我感觉我每个毛孔都在排斥,我几乎是夺门而出,跑到路边一阵阵的干呕。”
“但是好像别人并不注意到我,这也就省去我再解释了。到了夜里,因为离得比较远,我们就留宿在亲戚家中。白天音调孤长的丧乐,此时都回了家,大人们仿佛忘记了这本是一场丧事,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且不时有一阵笑声传出来。”
“我和妈妈住在亲戚家的二楼,可能白天她去主家帮忙,很是有些累,入夜很早就睡下了,而我因为比较认床,所以翻来覆去的一直清醒着。床靠在窗户边,我侧身睁开眼就能看到外面,那天夜里的月非常的清亮,光铺在被子上,就像一层发光的膜,我张嘴哈哈气,能看到一阵阵的白雾飘起。”
“百无聊赖之下,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间,我好似听到了一阵突兀的敲窗声,只一瞬间我就浑身汗毛直立,我们可是住在二楼呀!我胆子可小了,这时候我不敢一个人逞强,蒙着被子喊了妈妈两声,将她喊醒后,说了敲玻璃的事。”
“我妈就从床上坐起来,钻到窗户边左右张望,然后也不说话,就把窗帘拉了起来然后低头给我掖了下被角,只叮嘱我安心睡觉。可这时我哪里还睡得着,抱着我妈的手臂,一刻也不敢松,心里祈祷着赶紧天亮吧。”
“侧耳听了一会还好那声音没再出现,后来不知不觉的还是睡了过去。等到再醒的时候,床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清冷的房间仿佛有青烟缭绕,我知道妈妈应该去早起又去帮忙了,翻身看到开了一条缝的窗帘,我始终还是心有余悸,就想起身再把窗帘拉上,哪知到手刚刚摸到帘子那,突然又是两下清脆的敲玻璃声,那声音近的就像在我的耳边敲响,像半夜惊醒的叹息声,我一霎间僵在原地,随后接触窗帘的手指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的痛,我立马就缩回了被窝,整个人蜷的像一只虾,闭着眼睛,但这时我却又不敢大声呼叫,不知为什么,好像人总不愿意率先去打破肃静。”
“我蒙着头,仔细的听着,但是除了我激烈的心跳声,刚刚两下急促的敲打声却已经无影无踪,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缓慢的从被窝中露出双眼,眯眼看向窗户,透过缝隙发现除了皎洁的月幕,却再也没看到其他东西。”
“突然这黑暗中又传来了一阵由远而近爬楼梯的脚步声,我以为是妈妈回来了,正当我松了一口气时,那脚步声到了房间门前却停了下来,等了一会,再也没有动,我渐渐的开始慌张,这时又一阵若有似无的木板摩擦声传来,‘吱呀……’,我知道那是房门开了,是被从外推开了,我小声的喊了下‘妈妈?’然而黑暗中却并无回应,当时的情况实在是诡异,我索性咬咬牙壮着胆子,借着月光摸到了床头边的灯,一下子就拉亮了暗黄的灯泡,空荡荡的房间立马呈现在眼前。”
“入眼是雾蒙蒙的一片,但隐约能看到房门已经张开了一条墨黑色的缝,而且那刺耳的摩擦声并未断绝,丝丝缕缕的仍钻入耳中。”
“陌生的房间里我就这么缩在被子中,露出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渐渐张开的门缝,也不言语。”
“门开到一半时,我大概已经松懈了下来,门口的黑暗中什么也没有,可能只是穿堂的风把门带开了吧,我这么安慰着自己。”
“起身穿上拖鞋,飞快的跑到门边,准备重新将门合上,可谁知就在我手快摸到门的时候,那木质房门一瞬间全部张开,门板狠狠的摔在了墙壁上,那声音真是及其的大,我直接被吓的一愣,随后就大声的哭了起来,转头就往床边跑去,接着又钻进了被子,颤颤巍巍的抽泣没几下,平白无故的一阵拍被子声音又响了起来,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崩塌了,穿上鞋子边哭边往楼梯口跑,我想到我妈妈那边去,那边人多怎么都比这边一个人好。”
“刚跑到楼梯口,一阵刺鼻的油漆味直往鼻子里钻,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墙上的开关我没摸到,但是我也不想停留了,只得借着楼下堂前微弱的光来趟过黑暗,下楼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能十几秒,过程中隐约能听到身后似乎跟着一阵脚步声,我停了下来,颤抖着回头看,空荡荡的楼梯上,夜似乎能把人吞没,入眼除了一阵阵的青烟,其余什么都没有。”
“刚回过头下楼,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就撞在了我身上,直把我挤到了楼梯护栏那边,我惊叫了一声,定睛看到一个暗红色的狗一样大的事物,就这么停在楼梯底下,起起伏伏的蹦着,一点声音都没有,就那么蹦着,它可能也注意到了我,随即就窜进了堂前,经历了这一幕,我停留在楼梯上不知道是该上去还是该下去,犹豫间,楼上的房门又狠狠的关了上去,直震得我耳朵疼,我开始闭着眼歇斯底里的喊着我妈,但是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已经没力气再大声喊叫,只得慢慢踌躇着往楼下去,越接近堂前,油漆味道越发的重,刺的我双眼发花,等走进昏黄的光里,我终于还是看到了那厚重的暗红棺材。”
“只一刹间,我觉得这铺天盖地的气味和入目刺眼的暗红,都像是要把我吞没,我的大脑天旋地转。地上的黄稻草开始扭捏蠕动,篮子上的鞋不停晃悠,燃着的油灯火苗渗着绿,盖在棺材上的花布滑落在地,纱帐被细风吹的左右拂动,供桌上的纸人一阵摇摆,终究还是倒在了桌子上,红扑扑的脸转向我,细细的眉毛,长长的眼线,咧起的嘴角,若有似无的一声轻笑,一切的一切都让我炸了锅一样的往门口跑去。”
“院子里烧纸钱的锅子旁,就有着那个暗红色的事物,只一斜,就翻过围墙,窜出了院子,随后我就站在门口大声呼喊着妈妈,这次她很快给了回应,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断断续续的和她描述了事情经过,听完她只让我别多说,带我回头对着灵堂下跪叩拜,然后通知主家来人重新摆好了纸人,铺好了红布,她则带我回楼上换好了衣服,天一亮就送我回了家。”
“从那天开始,我发了一个礼拜的热,去医院也看不好,后来我妈听村上洗菜的老人家说,找了个看大仙的婆婆,给我浑身拍打了一阵,又倒了杯热糖水给我喝,次日就没再发热了。这件事过了到现在,我就没再遇到奇怪的事,但是却时常能闻到一股油漆味,真的,不骗你。”
我听她讲完,只轻轻的拉起她的手,说:“太阳快下山啦,回去吧!”“嗯,回去吧!”
后来没几年,她跟着家里大人搬去了大城市,我们就再也没联系过了,但是我仍旧记得那些傍晚,她走在我前面,夕阳暖红的光透过她的短发,铺成了我童年记忆海的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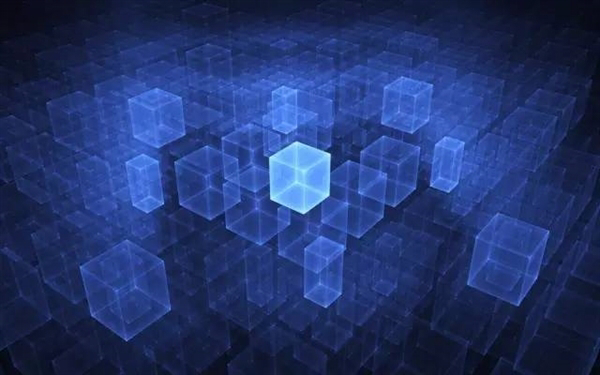














文艺成分太多,把节奏拖得好慢,这看起来就像是课文一样了,这事情里面遇见的就是抢夺丧礼祭品的其他鬼
嗯
像是真的,又像是写了篇灵异类的作文
哈 姑妄听之
文笔真好…
很美好的文章!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