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辛酉
(申明:所发故事均由庚申辛酉原创,版权均为作者所有,不得洗稿、抄袭,侵权必究)
奶奶的娘家在新沟村张家。听父亲说,我们队上的几户张姓人家和奶奶的娘家是同一个张家,所以父亲每次在路上遇见张家爷爷都喊舅舅,那我应该喊他舅爷。
张舅爷是家里的独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听队上的人讲他是一个干啥事都很消停(方言,指不管做什么都不紧不慢,安静从容),就连吃面条的时候,他都是把碗里面条捋顺了以后,才开始吃。
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生产大队挣工分,生怕活干少了工分少,年底分的粮食少。所以每次上工(方言,指生产大队上地干活的意思)的钟声响了,大家都匆忙拿上工具往门外走,而张舅爷还在吃饭,吃了一碗还不够,还要再吃一碗。
时间久了,生产大队长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晚上干的活,吆车。
父亲是六四年出生的,而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工分制,每家每户还要给供销社完鸡蛋和猪肉的任务,粮食可以按平时挣的工分在年底的时候挣回来,可是平时买布和其他生活用品的钱却只能靠完成鸡蛋和猪肉的任务,才可以赚一点回来。
那时候鸡蛋的任务要按月完成上交供销社,一口人一个月要上交两斤鸡蛋,一个鸡蛋可以换回5分钱。而到了年底就得完成猪肉的任务,以一斤猪肉8毛钱的价格换回一些过年的钱,同时供销社还会回馈养猪户一些红薯皮作为猪饲料。
父亲说那个年代,什么垫圈、出圈、挖地、拾粪、压粪的活他们都要干。
其中垫圈就是用手推车把土推到生产大队里的牛圈。等到秋天农忙结束了,再用手推车把牛圈里面的粪土推到耕地里,这叫做出圈。
而挖地是个辛苦活,就是用铁锹把地翻一遍,身强力壮的人一天可以挖八分地,一般人一天铆足了劲也就五六分地。
拾粪不仅要在农村周围活动,还要去城里的公厕等着。因为那时候没有化肥,生产队所有的耕地用的肥料都是人工肥、出圈出来的牛粪肥,但就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年粮食打下来后,要完成国家的任务粮,剩下的才是整个生产大队里每家每户的口粮,如果肥料肥性不足,粮食产量低,那么大家分的自然也就少了,家里面人口多的人家是要挨饿的。
所以就产生了另一种造肥的方法,压粪。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北方雨水足,戈壁滩上的植被长得非常茂盛,有一种茎叶肥大的臭蒿子就被人们当做肥料,生产队队长会在霜冻之前,安排社员去西山口(地名,过了西山口就进了金昌市)那一片戈壁滩上割臭蒿,因为那时候的蒿草长得最肥美,茎叶看上去像是包了一肚子水,把这个割下来以后,一层土一层臭蒿压起来,经过发酵是上好的肥料,肥性很足。
社员们一般都是白天在戈壁滩上割臭蒿,晚上回来。这样子为了把当天割下来的臭蒿拉回生产大队,就产生了另一个挣工分的活,吆车(方言,指赶车)。
吆车一般指牛车,但有时候也有驴车。
北方由于昼夜温差大,在九月的时候早晚就已经很冷了,需要穿皮袄。有一天晚上,张舅爷拉着臭蒿往回走,他穿着皮袄坐在牛车的沿条子上(方言,指古代马夫赶车做的那个位置)丢着盹。晚上出奇的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四周阴沉沉的,黑夜想鬼魅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只能听到牛脖子上面的铃铛随着牛走路的步伐叮当叮当的声音,突然一阵鸱冠子(方言指猫头鹰,念chī ,)的呱呱声,像一个小孩子咯咯咯的在笑,张舅爷一下子惊醒了,抬手一鞭子,空中“口扁”(pià)的一声,顺便骂了一句,这个死娃子(方言),声音很快就消失在了黑夜里。牛车沿着旧的车轱辘印,缓缓的往前走着,张舅爷又开始迷糊了。
忽然,张舅爷隐隐约约感觉牛怎么不走路了,鼻子一直喘粗气,使劲的晃着铃铛。同时,张舅爷感觉有个人抓着他的胳膊在拉他,一边拉还一边说,“走,我们一起走”,想把他拉下牛车,张舅爷一边丢盹一边说,“我不去”。拉的那个人继续拉他,“走吧,我们一起走,你也给我做个伴”,张舅爷说,“你又想的把我拉上往死里填里嘛”,这话一出口,人立马清醒了,张舅爷猛地把胳膊往回一抽,拿起鞭子就是甩了几下,空中响起了鞭子声,拉他的那个人也不见了。
张舅爷一看,戈壁滩上遇见鬼了。于是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仅会的那么几句西北小曲(想吃些热肉了蒸锅里蒸,哎呦,蒸锅里蒸,吃羊肉能懂人的心),就这样觉也不敢睡了,甩着鞭子,唱着曲,匆忙往队里赶。
第二天在生产大队开会的时候,张舅爷和队长反映情况,说啥也一个人不吆车了,太害怕了,差点被鬼填死了。毕竟被鬼填死这样的事在队上也发生过。
说是在西山口那边放羊的两个羊倌,有一天下午放羊回来,一个人在饮羊(方言,给羊打水喝),就嘱咐另一个人先去住的房子做饭去了,等这个人饮完羊,把羊赶进羊圈回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提前回来做饭的人,抓着灶台上的灰,墙皮往嘴里,鼻孔里填,力气大的出奇,拦都拦不住,等到那个人去附近的车马店(从清河到金昌市的一个方便车夫休息的中间驿站,位于西山口,后期拍照片给大家看下),叫人回来时,人已经死透了,嘴里面填进去的土块泥巴都抠不出来。
就这样,生产队的队长安排了我父亲陪着张舅爷吆车。
父亲那时候十七八岁,狂得很,一边笑话张舅爷,一边说,“舅舅你就是胆小,这有啥好怕的,再说真有那东西吗”,张舅爷笑而不答。
农村有句俗话叫“锅盖揭早了,气冒掉了”,就是指人不沉稳。这不第二天傍晚张舅爷就带着父亲从西山口吆车往回走了,父亲坐在铺了一块羊毛毡的蒿草上,张舅爷坐在车沿条子上。牛慢悠悠的走着,生怕天不黑似的。
慢慢的太阳下去了,周围也慢慢开始黑了。
这时候张舅爷说,“外甥子你看下你的四周”。父亲向周围看了一圈,头皮都发麻了,周围的戈壁滩上,一个个黑壮壮的东西,就像烧黑的半截树墩杵在戈壁滩上,随着牛车的移动,正一步步地向他们靠近,可是一靠近路边就感觉有一道无形的墙,挡着这群邪祟,愣是他们想挣扎靠近,也无济于事。父亲吓得赶紧把头缩进衣服了,头都不敢抬。张舅爷笑着调侃道,“外甥子,怎么样,你胆子大怕什么,要不再看一下”。就这样,张舅爷赶着牛车不紧不慢,消停地走着,而牛始终在路的中间,沿着之前的车轱辘印。
一直到了西沟四队的位置,就算是进村了,这时候月亮也升起来了。张舅爷推推父亲说“外甥子,不要怕,你知道为啥那些东西过不来吗,因为灶有灶神,山有山神、路有路神,我们一直在路中间走,有路神护着我们,它们不敢怎么样。但是一旦我们走出了路,那路神就管不了了,我们也就交代了”。父亲听到这,抬起头看着张舅爷的脸,似乎也没那么胆怯了,然后和张舅爷喧着慌,在月光的陪伴下回队里了。
张舅爷前几年过世了,一生无病无痛,算是寿终正寝,在我的映像中他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这个故事表达下辛酉对老爷子的惦念。
老爷子说的对啊,我们只要在路上走,不出路,邪祟永远粘不了身,因为有路神护着我们。人生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走正路,一身浩然气,定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如若禁不住诱惑,出了路,走上邪路也是迟早的,这样被邪祟祸患也就犹未可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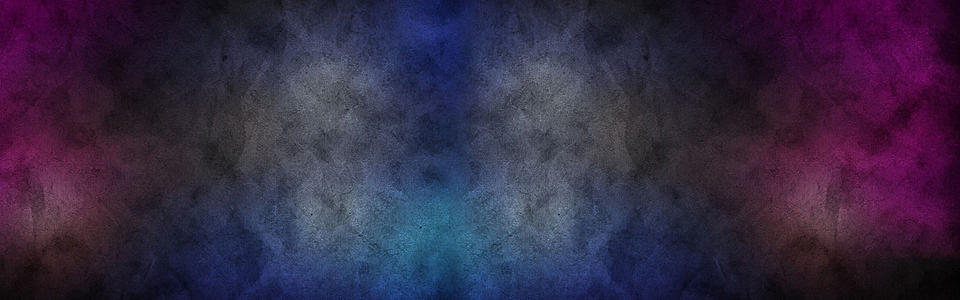




舅爷厉害!广东也有句俗话:天上雷公,地下舅公。意思是舅公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意思。舅爷有的地方也叫舅公,舅爷这个辈分确实是有分量的。
听你这么一说,舅公可以辟邪?
不是,是辈分高而已,不能辟邪。
辛酉这个舅爷无疾而终,还是做了一些功德事的。荒年的时候家乡饿死人,他背地里也算是一个背尸人,后面的故事慢慢发出来。
那时候一个鸡蛋5分钱,可能也抵现在最少一元钱一个鸡蛋。
资源匮乏的年代,我大伯是村里的会计,也算是个读书人。据说是后来还要读的,结果学费需要两个大洋,读不起就没读了。
好象两个大洋可以买好几百斤米,听说的。
作者是甘肃的?